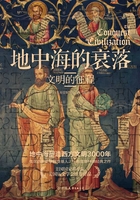
十一、苏美尔人及其与闪米特人的冲突
今天,我们只能通过古巴比伦城的遗迹与泥板上的古老文字来追述古代的城市生活了。在肥沃新月,苏美尔人和闪米特人之间旷日持久的斗争只不过是游牧人与高地人之间众多斗争中的一种而已。
北部高地人并不是闪米特人,我们至今也没有发现他们与阿拉伯沙漠中的游牧闪米特人之间的联系。但是从外貌上而言,他们属于白人。这些北部高地人有着高原地带人种的常见特征——呈圆形的头部。但是我们现在还没有确定他们的族系。我们可以在一些残存的石刻上看到,他们的脸部很干净,穿着粗毛制成的裙子。我们现在可以确定的是,他们之间有一些苏美尔人。那时的高地人还处于使用石器的阶段,但其中的苏美尔人很早就开始经由东部和北部的山口进入两河流域了。这些苏美尔人中的一部分可能在底格里斯河的河岸定居了下来,一部分甚至到了北边的亚述,还有一部分则抵达了冲积扇平原。让我们感到惊奇的是他们早在公元前3000年以前就开始开垦两河河口的沼泽地了。希纳尔平原的南部地区逐渐被他们占领,这片区域后来被称为苏美尔。
图82 古巴比伦人的播种机[仿克莱]

两头牛拉着播种机,旁边有一个农夫在赶牛并引导方向。在播种机的后面站着的是操作者,他扶着播种机的两个把手,操纵着播种机前行。播种机在移动的时候,会在土地上犁出较浅的垄沟。播种机上面有一根直立的管子(a),管子的上面还有一个漏斗(b),有一个专门的农夫负责在旁边往漏斗里撒种子,种子从管子中漏下,然后就落入了垄沟中。这幅图是在一个小石印上发现的。
由于底格里斯河河岸太高,不利于饮水灌溉,于是苏美尔人选择了幼发拉底河。他们沿着幼发拉底河的河岸盖起了一间又一间的低矮泥屋。在这里定居的苏美尔人学会了利用堤坝控制洪水,掌握了通过开渠引河水灌溉的方法,还学会了种植和收割成片的作物(图82)。这时,他们已经开始种植大麦和小麦并把它们作为主要的粮食作物,这与埃及是完全一致的。有意思的是,他们用埃及的名称来命名破开的麦粒。那时的苏美尔人已经有了家畜,他们生活中的一个重要部分就是饲养牛羊(包括山羊和绵羊)。那时,他们的牛拉着犁,驴拖着车,生活过得充实而滋润。这里还首次出现了运载重物的轮子(3),但他们还没有发现可以运输物品的动物——马。通过与上游地区,可能是尼罗河谷的交往,他们拥有了金属。那时的他们还没有掌握将铜和锡熔合,制成更为坚硬的青铜的方式,但是他们的工匠学会了打制黄铜器皿。
图83 早期的苏美尔楔形文字泥板(公元前28世纪)

这块泥板是早期苏美尔城邦国家时期,即将进入萨尔贡一世时的作品。泥板上的记录是那时的商业账目,其中的圆圈、半圆以及其他圆弧符号代表着各个数字。这些符号都是通过苇尖笔的上圆端在泥板上印出来的。这时图中的符号已经是由一系列的楔形线组成的了。
出于贸易和行政管理的记录需要,苏美尔人学会了用粗制的草图做记录。一开始,他们用扁平的椭圆形或圆形黏土片和苇尖做成最原始的“纸笔”。这种黏土做的记录在太阳暴晒后会变硬,在经过炉火的充分烘烤后,这种黏土会变成不易磨损的记录泥板(图83)。我们至今还能在泥板上看到一些原始文字(图84)。这一点也与埃及非常相似。他们用芦苇制成的尖笔在泥土上记录图形,他们首先将芦苇斜着切断,形成一个尖尖的形状,然后将苇秆劈开,尖笔就完成了。但是这些图形并不是用芦苇尖刻画在泥土上的,而是印在上面的。他们把苇秆的一端先压在黏土板上,然后把有尖的那一端也压进去,然后泥土上就会出现一条线,并形成一个三角。因为黏土板上的三角形与楔子很相似,于是这里的文字被称为楔形文字。我们会发现,苏美尔人记录的每一幅图形都是由楔形线组成的。例如,在他们的文字中,“星星”用符号表示,而代表“脚”的意思。(见图84,V栏第三图及I栏第三图)。在使用过程中,这些楔形线构成的图形越来越复杂,而随着书写速度的加快,楔形文字就变得越来越潦草而难以辨认。于是,后来的楔形文字与先前图形的相似特征逐渐模糊,甚至慢慢地消失了。
这时,文字由图形阶段逐渐向语音阶段过渡。最后,苏美尔文字一共包括了三百五十多个符号,每个符号代表一个音节或单词(4)。也就是说,每个符号代表一组音素。苏美尔文字体系中从未出现过字母表,因此,我们可以在该体系中找到像kar和ban这样的音节符号,但是找不到k、r、b、n这样的字母符号,而只有这些字母符号才能组成音节。由此,我们不能像讨论埃及文明时那样,为苏美尔文字总结出一个字母表。
图84 早期的巴比伦符号及其图像原形[主要源于巴吞]

第一列是最早的形式;第二列是开始与原图形分离,出现楔形线的形式;第三列是最晚的完全由楔形线组成的形式,这时已经完全看不到原图形的痕迹了。例如,第一列的原形V、VI和Ⅷ的特征还能在第二列中看到,但已经无法在第三列中看见了。
我们可以在这些泥板上的记录中发现,苏美尔的抄写员们通过按月记录来计算时间,每当新月出现时,他们就开始一轮新的记录,满12个月即合为一年。我们在前面提到过,这种方式合计的12个月实际上是不满一年的,于是,当发现距离年末还差一个月时,他们会在记录里再额外加上一个月。这种记录方式既不便捷也不精确。后来,这种日历被犹太人和波斯人继承下来,并被东方的犹太人和伊斯兰教徒沿用至今。与埃及人一样,苏美尔人也通过当年的重大事件而不是时间顺序来纪年。
苏美尔人的数字系统使用的不是十进制,而是六十进制。于是,他们的大数字是由许多个六十组成的,这与我们用二十计数很类似。如今,我们对于圆周的分割(六乘以六十度)以及对于时、分、秒的计量也是沿用的六十进制。苏美尔人最主要的重量单位是米纳,一米纳等于六十个谢克尔。我们的磅就相当于当时的米纳,只是我们引进这种计量单位后给它换了一个名字。
巴比伦人在希纳尔平原的中央建了一座高塔。这座塔高300多英尺,底部周长300英尺。由于巴比伦没有石头,因此他们使用砖块建成了这座塔,烧制而成的砖块砌成的表面可以抵御风雨的侵蚀。这座高塔整体上呈现正方体形,塔身由下往上不断地小范围地变窄。塔前有三段阶梯,大约有150英尺,十分高大,三段阶梯在高塔的入口汇合,而入口几乎是建在塔前部的半腰处。塔的顶部是一个方形庙宇,庙宇的前面是一个露天的厅堂,后面是供奉神灵的地方。这种建在塔顶的庙宇被人们称为塔庙。这里的第一座塔庙是尼普尔的塔庙,它是恩利尔神的祭坛。恩利尔是苏美尔至高无上的大气神,因此,对于苏美尔人来说,这座塔庙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所有的苏美尔部落都崇敬塔庙。在进入巴比伦尼亚平原之前,苏美尔人是住在山里的,他们对于山里的一切都已经非常熟悉了,因此,他们在进入平原之后,还试图用山的样子来建造圣坛,并以此来表示自己对大气神的虔诚与崇拜。就是在这种想法的支配下,尼普尔的第一座塔庙建起来了。后来,其他城市也接受了这种思想,于是塔庙就开始出现在整个巴比伦尼亚平原上。至今,关于巴比伦塔的神话故事还在希伯来人之间流传。宏伟的巴比伦塔代表了一种新的建筑观念,为建筑艺术做出了重大的贡献。后来的教堂尖塔就是在它的基础上演变而来的。
图85 柯底威绘制的通天塔复原图(以最新的发现为蓝本绘制)

巴比伦塔的遗迹现在已经很难寻觅,因此,没有人知道它的原型究竟是什么样子。在古阿舒尔城被发掘出来后,人们认为巴比伦塔很有可能是四面被斜面环绕的方形的梯式建筑。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巴比伦泥板被发现,人们开始了解了通天塔(至少是巴比伦城塔庙)的确切尺寸。柯底威是巴比伦的发掘者,他还发现了马杜克神庙的正方形地基以及塔庙三段阶梯的底部。柯底威教授在新发现的基础上,结合了乌莱率领的英美探险队在乌尔塔庙前发现的类似的三段台阶,绘制了一幅新的复原图。柯底威教授在1925年去世了,他的代理人同意在本书中发表这幅图。巴比伦城的马杜克神庙侧宽300英尺,高300英尺,体积为92立方米。这可能就是早期塔庙,尤其是尼普尔的塔庙所特有的神圣尺寸。
塔庙的周围有一系列的附属建筑,包括贮藏室和神庙事务的办公室等。为了让神庙免受干扰,塔庙及其附属建筑被四周的围墙与城市隔离开来。这座神庙由僧侣管理。这些僧侣们特别富有,他们掌管着塔庙的土地和财产,还有一些抄写员给他们做助手。国王或者城市的统治者也出身于僧侣,他们的地位比僧侣要高,人们称他们为“帕泰西”。帕泰西既要负责神庙事务,又要治理城市社区,因此非常忙碌。
农民们常常来到神庙,在祭坛上奉上自己的供品。这些供品包括山羊和装着几枝棕榈树枝的水罐,这样的水罐是土地繁荣的象征。农民的祈求大多与土地相关,他们祈求河水上涨,润泽土地,也祈求土地肥沃,永葆丰收。后来,这种装着棕榈树枝的罐子演变成为“生命之树”。这种象征符号时常出现在希纳尔地区的遗迹中。朝圣者向土地神、空气神、天空神和海神祭拜,他们祈求神灵保佑他们免受洪水的危害,也祈求风调雨顺,年年丰收。这是因为他们的父辈告诉他们,神灵们曾经放任河水泛滥,吞噬他们的土地,让他们遭受了巨大的灾难。于是他们形成了洪水忧患意识,这种意识被后来的希伯来人继承了下来。
图86 巴比伦尼亚的丧葬风俗

这里的人们死后的棺材就是两个开口对接的大陶罐。有时,死者被葬在用土坯垒成的简陋墓室的底部。那时的人们死后不会埋进坟场,而是埋在家里的庭院地下或房间的地板下。所以,我们现在很难找到巴比伦尼亚的坟墓,随葬品更是少见。在少数的墓穴内也有一些陪葬的陶罐或铜罐,有时还能发现一些金银或珍珠母制成的装饰品以及一些武器和工具。
在宗教方面,我们还应该注意到一点:苏美尔人的丧葬方式与埃及人非常不同。苏美尔人死后就埋葬在城里,甚至就埋在自己的庭院里,或房间的地板下(图86)。苏美尔的死者没有自己的墓穴,也没有棺材,更不存在大量的能带去另一个世界的陪葬品。对于苏美尔人来说,死后的世界是地下的一个黑暗而肮脏的地方。无论高低贵贱,人们死后,都要去到那个混沌的世界。我们都知道,埃及人非常重视墓葬,坟墓内通常伴有考究的随葬品。因此对于古埃及的历史研究而言,埃及的墓葬意义重大。然而,我们无法在巴比伦找到这样的陪葬品。
塔庙的围墙外面就是市民的房屋,这些民房从塔庙的围墙外往四周延展开去。民房大多为长方形的建筑,建筑材料是晒制的砖块(图87)。每座房子的北边都建有一个庭院,庭院的南侧建有一间主屋,主屋可以通向各个房间。这个城镇最初只有几百英尺宽,后来不断扩张。大部分城镇都建在人工堆成的山包上(图88),了解这一点对我们今天的研究有着重要的作用。
图87 早期的巴比伦房屋的复原图

早期巴比伦城镇的规模很小,城镇中的房屋大多用土坯建成,装饰也比较简单,例如垂直的嵌板和墙顶上的齿状边沿等等。与埃及不同的是,巴比伦房屋使用的是拱形门洞,虽然埃及人也知道拱顶的制作方式,但他们更偏向于平顶的门洞。
晒制的砖块是整个古代世界的主要建筑材料,而且在今天的东方仍然被许多普通民房用来垒墙。但是用这种砖砌成的墙面不能抵挡风雨的侵蚀,大部分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倒塌。因此,每次暴雨侵袭,总会有古屋被摧倒。即使是对于现代人来说,房屋坍塌后的应对办法就是把倒掉的房子铲平,然后在原来的地方盖一间同样的房屋。这种方式持续了几千年,耶稣就曾经在寓言中描述过这种房屋坍塌的情景(《马太福音》7:27)。许多年后,坍塌的房屋把村庄垒成了一个大型垃圾堆,而垃圾堆的上面就建着城镇。
至今,这些古代的人造沙包上还保存着许多东方古代城镇的遗迹。在那些古老的国家,这种山包随处可见,它存在于特洛伊、巴勒斯坦境内的耶利哥、哈密吉多顿或美吉多,以及埃及的安利芬坦。同样,它也遍布于如今的巴比伦尼亚。这些山包早已经被遗弃,只剩下一片荒凉。我们可以在图88中看到它们现在的模样。
图88 古巴比伦尼亚,尼普尔城的房屋废墟形成的山包

前面的空地曾经是一个大庭院或者广场,如今长着一些零落的沙漠灌木。过去人们常常来到这里交易,卸货或者进行其他的公共活动。远处的山包下面是尼普尔神庙的主要建筑,它占据着神庙的南部,最高点以下是以前的神庙峰。只有一些位置较低的部分神庙在山包下幸存了下来。大约在5000年前,这些山包下面的建筑中,官员和书吏们在忙碌地应对城中所有的事务。在图89中的庙峰顶上可以俯瞰整个神庙区。
图89 对古尼普尔城遗迹的挖掘

在1889年到1990年之间,费城大学探险队先后三次对古尼普尔城进行发掘。这幅图描绘的就是正在进行挖掘工作的情形。曾经用来垒墙的土坯被不断挖出,由当地的民工用箩筐运往远处的土堆。曾经被掩埋的建筑残余逐渐显露出来。在挖掘的过程中,时常会出现一些泥板和陶质或石质的器物。古巴比伦尼亚的记录和古物得以重见天日了。不同的地层埋着不同的古物,最古老的在最底层,年代较近的则埋在相对较浅的地层。这幅图是从图88中最高的山包顶上看到的情景。我们可以在废土被运走的那一部分看到广阔的地平线,由此可以想象,昔日的巴比伦平原是多么平坦。此前,保存在欧洲的巴比伦尼亚与亚述的古代文物只占了一个展柜,面积只有几平方英尺。而1840年以后,考古队挖掘出了大量的古文物,将更为真实的历史展现在我们面前。
在那个时代,泥板随处可见。人们用泥板来记录家务、写信、记账、开具收据、写便条等等。房屋倒塌时,将泥板压在了下面,于是现在的山包中还埋着许多泥板。大部分掩埋在庙宇或公共建筑中的文件记录了政府的重要事务;而发现于统治者的住宅或办公室的泥板大多记录了战争或征服他国的战绩。有时,统治者会将自己建造的建筑物、获得的胜利以及其他辉煌的成就刻在泥板上,然后埋在某处建筑的地基下面,让后来的统治者们去发现。山包里除了文字记录外还埋着许多家用物品和雕刻艺术品。这些建筑物的废墟已经不能像埃及遗迹一样向我们展现那段古老的历史,但是,这些山包仍然是包含着丰富内容的大型文物仓库,在这个仓库里寄存着古巴比伦的伟大文明。下面就让我们来追溯这一段历史。
图90 苏美尔城国王的银质花瓶

这是早期巴比伦尼亚最精美的金属制品。花瓶表面的两条宽雕饰带代表着早期苏美尔的装饰艺术。在花瓶下面那条饰带上,一只狮头鹰抓着两头狮子的背脊,而两头狮子分别咬着一只羱羊。这是一种对称的动物构图,并且图中是正在掠食的动物,这是公元前3000年前苏美尔艺术的一个独特创造。在这里,鹰和雄狮是苏美尔拉嘎什城邦王国或者武器的象征。后来,这种对称的动物构图传到了欧洲,并一直流传下来。在今天的国王或者国家的纹章和武器上仍然有这样的装饰。在俄国、奥地利、普鲁士和其他欧洲国家,鹰的形象仍然频繁出现在武器上。5000年前的拉嘎什鹰流传到了美国,就成为“美国鹰”。
掩埋在山包最底层的是苏美尔人的石雕作品。这些作品大约创造于公元前3000年,他们那时刚刚开始进行石雕创作,因此作品还显得比较粗陋。后来,随着个人图章成为日常交往活动中的必要信物印记,石刻艺术也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从在石头上雕刻图章(图91)到在石头上绘制小型的图案,雕刻艺术迅速地发展起来。人们将擅长雕刻的工匠称为宝石工,很快,早期苏美尔的宝石工就成为古代东方世界的这一行业内技艺最高超的工匠。这些宝石工的创作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我们的装饰艺术,我们至今仍然能够看到这种工艺。苏美尔人不仅创造了石刻艺术,他们还能在金属制品上进行雕刻,他们雕饰了许多精美的金属制品(图90)。
图91 早期苏美尔的圆筒印章

早期的苏美尔人不是直接在泥板文件上签名,而是用小型的石头滚柱和滚筒来签章。滚柱和滚筒上刻有图案和主人的名字,主人只需要把这样的圆柱印章在松软的泥板上滚动,图案和名字就印在泥板文件上了,这与签名的作用是一样的。人们在巴比伦尼亚废墟中发现了许多这样的石滚印章。在对这些印章进行研究之后,我们发现,巴比伦艺术大约经历了从公元前3000年到公元前500年之间共2500年的兴衰历程。这幅图的左边是石滚印的一端,右边是石滚的一面。
曾经喧闹繁华的古巴比伦城如今沉寂在沙丘之下。我们只能依靠残存的遗迹与泥板上的古老文字来追述那遥远时代的城市生活了。在最早的泥板上,我们发现了一个自由民阶级,这个阶级居住在城市里,拥有自己的土地,用大量奴隶来为他们耕种,还与沙漠中的商队和河上的船只进行自由交易。他们就这样过着自由闲适的生活。官吏和僧侣的地位比自由民高,他们是城里的贵族阶级。这些贵族拥有城市周围几英里的土地,当他们聚在一起时,就形成了一个社会,这样的社会被称为城邦。因此,这一地区最早的文明阶段被称为苏美尔城邦时代。由于我们还没有弄清楚所掌握的最早的巴比伦文献的确切日期(5),因此这一时代的起始日期也没能得到确认。但是那些巴比伦早期文献告诉我们,苏美尔城邦时代有可能要追溯到公元前32世纪。我们所有的文献都来自巴比伦尼亚历史上最早的城邦之一——乌尔。乌尔曾经有一个名叫安尼帕达的国王,乌尔城外的一间郊区庙宇中立有一块安尼帕达时代的石碑,这块石碑可以追溯到公元前31世纪,那上面的碑文是迄今发现的亚洲最早的皇家记录。城邦时代一直延续到公元前27或28世纪,持续了几百年的时间。
图92 率领部队方阵的苏美尔城邦国王(大约在公元前2900年)

这幅图的右边是国王,国王的脸部已经脱落了。在这幅图中,国王走在方阵的最前面,他的身后跟着一队士兵。在古代亚洲战场上,士兵们组成的这种被称为“方阵”的作战单位是战争史上的首创。此前的许多个世纪,古代人的战斗一直是散漫而不规范的,而要将兵力集中起来组成方阵,就必须对士兵进行严格的训练,并制定严明的纪律。这时候的埃及还没有出现这种阵法,也没有严格的训练。图中的苏美尔士兵没有带弓箭,他们手握长矛,头戴盔帽(可能是皮革制成的),一字排开,向前行进。他们的手中还挽着高大的盾牌,几乎能挡住他们的全部身体,这无疑增强了他们的防御能力。图中的士兵们正从敌人的尸体上踏过,这说明他们正在消灭敌人。这幅图是刻在石头上面的,我们可以发现,那时的巴比伦尼亚和苏美尔的雕刻艺术还比较粗糙,而此时的埃及正处于金字塔时代,肖像雕刻已经取得了辉煌的成就。
在当时的众多城邦中,苏美尔城邦处于领先地位。南部的许多城邦联合成了一个城邦群,他们占据了苏美尔地区。这些城邦群沿幼发拉底河分布,因此后来掩埋着城邦废墟的山包形成了一条蜿蜒的曲线。虽然城邦贵族不断地压榨人民,并对其收取重税,实行不平等的政治制度,但是统治者(帕泰西)的历史功绩并不能因此被抹杀。城市中的许多事务,尤其是战争和水利灌溉都要仰仗帕泰西的统一管理。灌渠和堤坝需要不断地维护和修缮,这种护理一旦中断,灌溉系统就会受损,水源因此被切断,农田就无法得到灌溉,因此农民也无法播种,更不可能收获。这种情况下,整个城邦就会面临饥饿的威胁。在战争方面,我们可以在墓穴中的绘画上发现,大部分城市的统治者会亲自率领军队上战场,那个时代的许多城市统治者都相当英勇果敢。战士们在统治者的率领下,斗气昂扬。他们头戴帽盔,身着盔甲,一手持枪,一手挽盾,排着方阵,无比威风地向敌军方位前进(图92)。尼罗河畔孕育了最早的高度发达的和平艺术,而苏美尔人创造了人类历史上最早的高度发达的战争艺术。一旦他们发现邻邦试图侵占他们的土地,哪怕只是蛛丝马迹,他们也会迅速采取行动,自发地聚集在帕泰西旁边,发誓要随他冲锋陷阵,坚决抵抗侵略者,直到把敌人赶出自己的领地。城邦之间的领土争端从未停止,因此,在公元前28世纪前的几百年里,苏美尔的早期历史就是一部城邦斗争史。
虽然苏美尔各城邦之间领土争端不断,但在特殊时期,各个城邦也会联合起来共同对抗外敌。沙漠中的闪米特游牧部落很早就在苏美尔北部一个名叫阿卡德的地区定居了下来。因此,巴比伦尼亚最早的闪米特人被称为阿卡德人。克伊斯是阿卡德最古老的城市,它位于两河最靠近的地方,是古代从两河通往东部山区的重要通道。克伊斯是第一座培育了一系列皇族和王朝的城市,因此在巴比伦尼亚的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最早的阿卡德人是沙漠中的游牧民族,他们既不懂得战术战略,也不会制定作战计划,但是他们面对的苏美尔人却具备十分高超的战争能力。在战争中,阿卡德人运用的主要武器是弓箭,他们因为害怕近距离作战,所以练就了一身高超的射箭本领。一旦敌军靠得太近而不能射箭,他们就会散开队形,与敌方肉搏,但是他们的队形非常散漫薄弱,根本不是苏美尔严密方阵的对手,因此常常战败。在那时的希纳尔平原上,北部是半定居的阿卡德闪米特游牧民族,南面是来自高地的苏美尔人,这两个民族之间水火不容,经常展开斗争。但他们之间的斗争只是发生在肥沃新月上的游牧人和高地人之间的斗争中的一种,这里还存在着大量其他的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