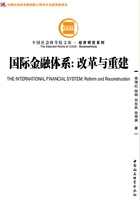
三 美元霸权的危害
美元本位存在诸多的问题,尤其对广大的发展中国家的汇率安排带来巨大的挑战。与此同时,作为世界最大的债务国,美国在不断累积其巨额的经常项目逆差,由此带来的美元贬值对国际金融体系带来巨大的风险。
(一)美元霸权下发展中国家汇率制度的两难选择
在美元本位下,发展中国家的“原罪”问题,尤其是东亚国家的“美德冲突”,给这些国家带来汇率制度选择的两难困境。
1.“原罪(original sin)”论
所谓“原罪”论描述了这样的事实: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缺乏发达的国内金融市场,不完善和脆弱的金融市场使得这些国家不能凭借本国货币向外国借款或获取长期贷款,甚至在国内也无法获取长期贷款。这就引发双重错配:货币错配和期限错配。[6]“原罪”论的精髓在于发现,双重错配并不是因为银行不审慎对冲它们的外汇风险,而是因为它们无法对冲。“原罪”论可以解释为什么金融市场不发达的国家害怕采取浮动汇率制度以及为什么政府通过保持汇率稳定来提供一个非正式的对冲。“原罪”带来的问题起源于小国,而且是债务国不能以它们的货币在国际上借贷并且经受着货币错配:银行借入美元,产生美元负债,而贷出的是本国货币;当美元短期负债额超过本币长期贷款时,遭受货币错位的债务人将有破产的风险。美元债务任何突然抽逃都会提高银行负债并引发破产。[7]
2.“美德冲突(conflicted virtue)”论
“原罪”论所描述的情形与债务国更相关。东亚的情形不同,东亚国家主要是债权国。由于所有东亚国家经常项目顺差很少得到相应的以本币形式持有的债权,这些国家私人或官方往往以美元资产的方式持有国外债权。然而,加入债权国俱乐部并没有使这些国家彻底放弃钉住美元的汇率制度。因此,就债权国而言,“原罪”则表现为“美德冲突”综合征:据有高储蓄率“美德”的国家往往同时具有经常项目顺差,并且这些国家面临两种结果:一是美元债权存量不断累积(因为它们的本国货币不能用于国际交易);二是本币面临国内外的升值压力。由于世界价格主要由美元计价,本币升值可能导致通货紧缩,从而丧失贸易竞争力。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将进退维谷,因为作为债权国,它没有切断与美元联系的选择余地。[8]
3.汇率制度有限的灵活性与重温1997—1998亚洲金融危机的教训
鉴于存在“美德冲突”,东亚钉住美元制是合理的选择。然而,1997—1998年爆发的亚洲金融危机暴露出这种汇率安排的一个严重缺陷,即存在开放经济条件下的三元悖论:在开放经济中,固定汇率制、完全的资本流动和货币政策独立性这三个目标中只有两个可以同时实现,任何企图同时实现这三个条件的行为都将导致一场货币危机。[9]亚洲金融危机就是处理三难困境一个典型的失败例证,即持续的资本流入引起东亚国家通货膨胀与货币升值的压力。为了排解这些压力,货币当局不得不采取冲销措施,但是事实上,在资本流动开放的情况下,政府的货币政策被“锁定”了,因为它们必须要服从于汇率稳定的目标。其结果是,在危机前的一段时期,这些国家的货币的名义值相当稳定,而它们的真实价值在那一时期已经被严重高估。
4.东亚国家的过去和现在:表象不同,问题依旧
亚洲金融危机过去十年了。现如今,亚洲国家的经济状况与十年前相比看起来大有不同。亚洲国家正经受着大量经常项目顺差,货币高估、期限和货币错位问题的严重性已经降低,外汇储备剧增。然而,在汇率安排灵活性依然十分有限的情况下,“亚洲国家正在从1997—1998年金融危机中学习错误的经验”。[10]换句话说,除非实施严格资本管制,如果亚洲国家坚持有限灵活汇率制度,货币政策独立性将难以为继。但问题是,资本项目自由化在许多国家已经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中国也不例外。
5.新两难困境
如果我们接受“美德冲突”论对为什么东亚国家不得不采取钉住美元汇率制度的解释,那么接下来的问题是,如何避免1997—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重演?亚洲国家似乎在“美德冲突”和三元悖论之间进退两难:在美元本位下,高储蓄的债权国不得不保持与美元的联系;而对美元过度的依赖,在资本项目自由化不断推进的条件下,将使货币当局失去货币政策的独立性,最终丧失对国内经济的调控能力。换言之,作为债权国,东亚国家没有切断与美元联系的选择余地;而对美元过度依赖,又使这些国家面临货币危机的风险。
(二)美元贬值导致金融动荡
世界市场过度依赖美元,这一事实使得美国在外汇市场上得以采用“善意忽视”的政策,从而导致美国和世界其他国家的努力具有不对称性。对美国这样一个大型及多元化的经济巨人而言,汇率波动如同一个轻微牙痛。它仅需要不时的修补,但从来不用动大手术。[11]然而,对一个依靠美元作为外汇储备以及贸易和金融交易计价货币的国家而言,它们不得不承担巨大的汇率风险。
1.美元贬值使世界范围的美元资产持有者承受巨大损失
美元的国际货币地位使美国成为世界最大的债务国,同时使其能够相对世界其他国家不断积累巨额的经常项目逆差。如何纠正大规模的经常项目?其途径之一使通过美元贬值来改善美国的贸易出口。事实上美元从2002年就开始了长期的贬值趋势。到2011年,美元的有效汇率贬值了35.7%(见图2—5)。

图2—5 美元指数
数据来源:美联储数据库。
伴随着美元贬值,美元资产价值不断萎缩,这也使美元资产的外国持有者面临负的财富效应。以欧元区为例,2004年底,欧元区所持美元资产总额近三万亿美元,相当于欧元区国内生产总值(GDP)的1/3(见表2—3)。如果美元相对于欧元贬值30%,则意味着欧元区要损失掉相当于其GDP的10%的财富。[12]
表2—3 美元资产的外国持有者(单位:10亿美元)

币值稳定是保持货币功能的重要因素。而美元正在丧失这一条件。历史经验表明,美元大幅度贬值都伴随着其作为主导世界货币的特权地位的动摇。[13]事实上,美元贬值是双刃剑:一方面,美元贬值有助于纠正美国经常项目逆差;另一方面,美元贬值造成美元资产价值的缩水,带来美元资产需求的减少,从而动摇美元本位体制。
2.美元贬值以及世界范围钉住美元助长了全球流动性过剩
2007年由美国次级债引发的流动性收缩,恰恰是多年来全球流动性泛滥的结果。美联储多年来的刺激性货币政策是全球流动性过剩的主要原因之一。钉住美元的新兴国家不得不跟随美国采取宽松的货币政策,因为这种钉住汇率制使美国能够向这些国家出口其货币政策。于是,当美元在2002年初开始贬值时,新兴市场国家被逼迫增加货币供应量以确保钉住疲软的美元。其结果,这种同步的货币政策进一步扩大了全球流动性泛滥。
3.对美国管理美元的能力的过分信赖具有脆弱性
传统的金本位制被视为一国保持温和通货膨胀最有效的国际货币制度,因为黄金供给有其自身限制。1944年至1973年,旧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的黄金—美元本位从局部上给各国政府强加了财政纪律。而当前的美元本位则主要依靠全世界对美国管理美元的信心。这是脆弱的,因为美元只不过是另一种货币,与其他货币不同的是,美元的地位要靠其他国家是否愿意持有它来决定。而接受美元的意愿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对美国政府能够维持低通货膨胀的信心。影响美国政府管理美元能力的任何因素都能在一夜之间使这种信心崩溃。
4.如果美元资产持有者减持美元,其后果如何?
美元资产的主要持有者之一是各国的中央银行。各国中央银行,尤其是亚洲国家的中央银行持有的美元储备通过以美国国债的形式实际上又流回到美国,成为美国经常项目逆差融资的重要来源。从另一个角度讲,美国的经常项目逆差的可持续性,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外国中央银行继续持有大量美国资产的意愿。这种意愿取决于两个因素:是否外国中央银行愿意继续干预外汇市场以防止其货币相对美元升值;外国中央银行是否愿意继续保持外汇储备中美元的最大的份额,是否进行了储备货币的多元化。事实上在一些国家储备货币的多元化正在小幅度进行,这对美元的本位无疑是一种动摇。但是,任何大幅度的美元减持都将伴随金融动荡,而金融动荡的主要受害者仍是广大的发展中国家。
总之,鉴于当前美元本位所面临的问题,我们需要美元以外的货币共同发挥国际货币功能,从而分散后布雷顿森林体系中的金融风险。那么谁是可能的候选货币?欧元,日元,亚元,还是人民币?
[1] 虽然日本是亚洲地区另一个大的贸易和金融交易伙伴,日元也是这一地区可自由兑换的货币,但日元在亚洲地区的使用十分有限。
[2] 参见Ronald McKinno,Gunther Schnabl.“The Return to Soft Dollar Pegging in East Asia:Mitigating Conflicted Virtue”, International Finance,Vol.7,No.2,2004,pp.169-201;Jeffrey Frankel,Wei Shang-Jin.“Yen Bloc or Dollar Bloc? Exchange Rate Policies in East Asian Economies”,in Takatoshi Ito and Anne Krueger,eds.,Macroeconomic Linkages:Savings,Exchange Rates,and Capital Flows,Chicago,1994,pp.295-329。
[3] Ronald McKinnon,Gunther Schnabl,“The Return to Soft Dollar Pegging in East Asia:Mitigating Conflicted Virtue”, International Finance,Vol.7,No.2,2004,pp.169-201.
[4] Eiji Ogawa,Taiyo Yoshimi.“Exchange Rate Regimes in East Asia-Recent Trends”,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的演讲稿(未发表),2007年9月17日。
[5] 其中,按官方公布的汇率制度划分,韩国采用的是浮动汇率制度;中国、新加坡和印度尼西亚采用的管理浮动汇率制度。
[6] Barry Eichengreen,Ricardo Hausmann.“Exchange Rates and Financial Fragility”,NBER Working Paper,No.7418,1999.
[7] 正如1997—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所发生的那样,这也能解释为什么1997年金融危机爆发前欠发达的东亚债务国选择钉住汇率制。参见Ronald McKinnon,Gunther Schnabl.“The Return to Soft Dollar Pegging in East Asia:Mitigating Conflicted Virtue”, International Finance,Vol.7,No.2,2004,pp.169-201。
[8] Ronald McKinnon,Gunther Schnabl.“The Return to Soft Dollar Pegging in East Asia:Mitigating Conflicted Virtue”, International Finance,Vol.7,No.2,2004,pp.169-201.
[9] 一些经济学家怀疑三元悖论的正确性,比如弗兰克尔认为,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很可能有同时实现三个目标的中间解。参见Jeffrey Frankel.“No Single Currency Regime is Right for All Countries or at All Times”,NBER Working Paper Series No.7338,September 1999。
[10] Nouriel Roubini.“Asia is Learning the Wrong Lessons from Its 1997-98 Financial Crisis:The Rising Risks of a New and Different Type of Financial Crisis in Asia”,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召开的“亚洲金融危机十年:教训和挑战”国际研讨会上的演讲(未发表),2007年6月21—22日。
[11] Benn Steil.“The End of National Currency”,Foreign Affairs,May/June 2007.
[12] Alan Ahern and Jurgen Von Hagen.“European Perspective on Global Imbalance”,paper prepared for the Asia-Europe Economic Forum conference,“European and Asian Perspectives on Global Imbalance”,Beijing July12-14,2006.
[13] 例如,在20世纪70年代末和90年代初,美元经历了两个阶段的贬值,在此后不久,美元作为主导货币的地位有明显的下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