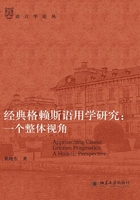
1.3 研究问题与方法
Grice的意义分析模式引入说话人因素来确定句子和词语意义,可以说是对意义的非客体化和对传统的颠覆。如果说Frege,Russell等人的著述是对人逻辑能力的重构,Chomsky的普遍语法是对人语言能力的重构,那么Austin和Grice等人就是对人语言行为能力的重构,是对理解何以成为可能的条件的重构。Grice是对人类理性行为的推理过程的理性构建(顾曰国 2010:xv),而不是简单的经验描写。Grice的意义分析,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两种分析模式(逻辑实证主义学派的真值意义理论与以后期维特根斯坦为代表的意义使用论)结合在一起,这本身就是一个创举(Thompson 2003)。
本书探讨Grice的意义理论,准确地说是探讨建立在合作原则基础之上的意义分析模式背后的东西,尝试集中回答的问题是:Grice的意义理论与理性观、价值论之间的内在关联是什么,这种内在统一性对于深入理解会话含义理论和意向意义理论有什么启示?含义理论赖以立足的合作原则的性质到底是什么?
早在《言辞用法研究》问世之前,Grandy & Warner(1986a)就尝试发掘Grice各个思想领域之间的关联性和系统性。他们(1986a:1)指出,作为哲学家,Grice的思想很有体系,不过他著作的系统性很少被人认识到。他们的目标就是要展示Grice各个不同规划之间的关联,关注点落在意义、推理、心理解释、形而上学和伦理学上。他们坦承自己粗线条的描述牺牲了Grice著作中具体而微的细节,仅仅勾勒了上述主题间的相关性。从他们的论述中我们并未获取一个明晰详尽的关联纽带。Grice(1989:F36-37)在论文集的前言中也提到自己理论间的统一性。他归纳了两个主题:一个是断言、蕴涵和意义,另一个是方法论,也就是采用语言分析的方法进行哲学研究。不过他没有展开,只是在“再论意义”一文提到了意义和价值之间可能的关联,再次把神秘留给了读者。在“反思性后记”中,他试图对文集中各论文间的连贯性做出阐述,但鉴于篇幅、时间和精力,也只是分门别类地简要概括出8个论题,其中的关联性没有得到相对明晰的勾画。Warner(2001:viii-x,xxxviii)尝试挖掘 Grice思想的连贯性与一体性,提及讲稿内部的关联性,没有进一步挖掘。Chapman(2005)是第一部系统介绍Grice思想的研究性传记著作,涵盖诸多方面,融Grice的生平、个性与学术历程为一体。作者提出探讨各个部分间关系的问题,给我们指明了方向[1]。冯光武(2006)讨论了意义和理性的关系,但对价值涉及的不多。陈治安、马军军讨论了理性在Grice思想中的地位之后,认为Grice著述之间的内在统一性仍需进一步探讨,关于理性、意义与价值理论间内在的统一性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2006:263;2007:65)。很多学者对Grice理性概念的理解有偏差,更没有揭示出这种理性假设与合作原则背后的关联,没有讨论Grice这种立场背后的深层原因(Allwood 1976;Attardo 2003;Kasher 1976,1977,1982,1987)。Neale(1992)对Grice(1989)意义和语言理论的发展脉络进行阐释,评议这部著作的重要性和一些有影响的反对意见。目的之一是力争把各个松散的目标联结起来,并为重新建构Grice思想提供思路,消除一些模糊和不确定性。他明确指出:“尽管 Grice 在‘后记’中尝试提供一些缺失的信息,努力打造各主题间的重要关联。但是若想以最佳的状态呈现 Grice的意义和语言理论,依然需要大量的发掘工作”(1992:511)。我们希望沿着这一思路走下去,尝试做出新的解读和贡献。研究的关注点集中在Grice 的理性观、价值论和以合作为基础的意义分析之间的纽带上,落脚点放在意义分析的深层背景和基础之上。
Grice的意向意义理论提出之后引起了一系列质疑和误解,这也证明了深入研究和整体把握的必要性与合理性。合作原则更是面临一系列的挑战,Grice因此被贴上了不同的标签。他被认为是理想主义者,不顾不同文化间的意识形态差异和价值观的不同,忽视同一文化中不同社会关系和权势关系,合作原则只是一种美好的愿望,不合实际或者是错误的,他的假定只是“哲学家的天堂”(Levinson 1983:102),“建筑师的草图”(Lakoff 1995:194),理性主体假设是先验的(Liu 2007)。研究者们对合作原则及准则的性质更是莫衷一是,见仁见智。有学者认为它们是规定性、道义性的;有作者认为是描写性的;还有把二者折中的(封宗信 2002,2008);也有人认为它们是理性重构,不是对会话主体心理过程的描写(Thompson 2008)。Horn(2004:7)指出,许多语言学家和哲学家都误解了准则的作用和本质。Green(1990)详细讨论了一些不正确的解读。我们认为,在整体视域下把握合作的性质,对其进行重新阐释,这一思路不仅合理必要,也是可行的。研究通过文献细读,整理Grice的语言哲学、哲学心理学和伦理学思想,给意向意义理论与合作原则以合理定位。
作为一位深邃的哲学家,战后日常语言学派的领军人物之一,Grice被视为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哲学领域新运动的精神领袖(Neale et. al. 1992)。他涉猎广泛,研究领域遍及语言哲学、认识论、逻辑、伦理学、哲学心理学、形而上学、哲学方法和意义理论等。他生前专于思考,轻于发表,在40多年的研究生涯中仅发表12篇作品。虽然著述不甚丰富,但涉及面广,影响深远。其思想体系博大精深,表面看起来错综复杂,但具有内在统一性。前面我们提到,先前研究者虽然指出他思想体系之间存在连贯和统一性,但并未深入挖掘。
Grice的思想观点鲜明,个性突出。然而,他的观点最初都以讲座形式出现,生前也没有专著出版,发表的文章年份相差较远,也不易得到。另外他的著述艰深,不太好统领和把握。还有一些手稿、讲稿和录音也没有来得及整理和发表。本研究在现有文献基础上,在整体论视角下,进行文献细读、提炼加工和梳理阐释,发掘其底层意义。在这种意义上,文献本身就是我们立论的事实依据和语料。作者利用在美国研修的机会,从Grice工作过的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Grice档案室获取资料,并与他的学生和同事[2]取得联系,获得邮寄资料,澄清了一些问题。这里的文献除Grice发表和尚未发表的著作、札记之外,还参考了他生前好友以及当代语用学和语言哲学领域相关权威专家的著述和评价,讲座、部分访谈录音资料[3],和学者对Grice的回忆等资料。
本研究是理论上的反思和梳理,采用整体视角,通过文献细读的方法厘清Grice思想之间的整体性和统一性,挖掘Grice的深层关怀,并尝试附以实例分析来支撑我们的观点。在这种意义上说,本研究带有语用学史个案研究的特征。
[1] 2008年夏Chapman在与本书作者交流时提到,自己没有把这一研究继续下去。她(2005:vii)写到,对Grice的著作了解得越多,对他思想中是否存在一个统一性,能把会话这个大家熟知的理论,放到更广阔更重要的哲学图景中的这样一个问题,愈发感兴趣。事实上Chapman(2005)就是围绕这一问题进行的初步探索和尝试,但是我们并没有从中看到令人振奋的结果。
[2] 其中包括加拿大约克大学Glendon学院哲学系的Judith Baker博士,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Searle教授,阿根廷的J. L. Speranza,后者是Grice研究小组主席,一直不遗余力地传播和推广Grice的学术思想。
[3] 这主要是指1983年他与Judith Baker,Richard Warner等人的谈话录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