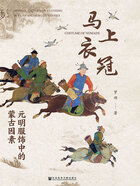
序二
一
“民以食为天。”但是,在“衣食住行”人类生存的四大基本要素中,为何排在首位的不是“食”而是“衣”?
因为“衣”是“文明”的人类与“野蛮”的动物的根本区别之所在。“食”代表的是生存,所有的动物乃至生物都需要;“衣”代表的是文明,甚至可以说代表着文明的程度,只有人类才具有。只是在我们过去的研究中,对“食”即生存的关注更多,对“衣”即文明的关注较少。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可能或多或少有“观念”的问题,即认为“食”是不能少的,“衣”固然也不能少,但“服”上加个“饰”,就有些“奢侈”了,而我们的民族应该是勤劳朴素的,是不能追求奢华的。虽然追求奢华不一定好,追求“美”却是人类乃至生物的共性。所以,人类的服饰既体现了文明程度,还表现出人类对美好生活的追求,成为一种文化的表现,用时髦一些的表述,是“物质文化”“物质文明”的体现。
关于服饰方面的研究,沈从文先生厥功至伟,《中国古代服饰研究》成了当代中国服饰研究的开山之作,成为后继者在这条道路上前进的基石。在这些后继者中,有罗玮和他的《马上衣冠——元明服饰中的蒙古因素》。
全书的主体是第一章“马上衣冠:元代服饰中的蒙古因素”、第二章“汉世胡风:明代服饰中的蒙古遗存”、第三章“遗俗流变:蒙古服饰的深层影响”,内容丰富,足见功力;前后有比较简略的“绪言”和“结语”;最后有“附录:元明衣冠服饰史料汇编”及“插图来源”。
二
相较于同类著作,罗玮的《马上衣冠——元明服饰中的蒙古因素》具有鲜明的特征。
其一,以往关于古代服饰的研究主要采用两种模式:一种是采用“历代服饰史”即“贯通”的研究模式;另一种是限于某个具体朝代即“断代”的服饰形制研究。这两种服饰研究模式皆有其合理性,而且都取得了重要的成果,但问题也是明显的。“贯通”式研究容易止于表层,往往只是在进行服饰形制等物质研究之后便浅尝辄止,并不涉及服饰背后复杂的精神文化现象。“断代”式研究的视野专注,却容易忽视服饰本身所具备的长时段、跨朝代继承和延续的历史属性。本书在前两种服饰研究范式的基础上,另辟蹊径,既不谋求“贯通”于中国历代,也不局限在某个“断代”,而是从民族文化的交融与传承角度,关注蒙古服饰对中国服饰本身和文化内核的影响。
其二,本书选取元、明两代作为服饰问题研究的基本时段,对蒙古服饰传统在元、明两代数百年长时段的影响和流播遗存问题进行了系统梳理。第一章“马上衣冠:元代服饰中的蒙古因素”探讨了元代服饰中的蒙古因素,通过文献史料和图像史料的梳理和比对,分别对钹笠帽、后檐帽、前圆后方帽、方笠、蒙古发式、辫线袄、答忽与半臂、质孙、系腰、兀剌靴、云肩、罟罟冠、蒙古妇人袍服等十三类元代影响较大的蒙古服饰进行了研究,充分结合了史料记载并展示了典型的图像史料。第二章“汉世胡风:明代服饰中的蒙古遗存”探讨了以上诸种蒙古服饰因素在明代社会中的存在、传播和流变状况,主要对卷檐帽、钹笠帽、直檐大帽、瓜皮小帽、瓦楞帽、辫线袄、曳撒、褶子衣、质孙、比甲等十种样式进行了深入探讨,并尝试对其行用阶层人群以及行用原因、社会心理以及所反映的政治文化背景等进行初步探讨。第三章“遗俗流变:蒙古服饰的深层影响”初步探讨了明代士大夫对蒙元服饰遗存的认知,揭示了所谓清代满洲服饰,其实很多是蒙古服饰在元明两代流变的结果。这为作者以后的服饰史研究留下了余地。
其三,本书广泛收集和研究大量实物、图像和文献史料,在一百五十多幅各类图像中,许多为第一次在服饰研究著作中展示。这些实物、图像、文字材料证明,元朝时期,蒙古族具有鲜明北方游牧民族特色的服饰式样对当时的中国社会服饰行用状况产生了重要影响。而且,蒙古服饰并没有随着元朝的崩溃而在汉地销声匿迹,相反,以不同形式继续在明代社会中广泛传播流用,其影响甚至延伸到了清代。蒙古民族“马上衣冠”的影响,不仅仅限于“服饰”本身,也涉及更为广泛的社会文化层面。
其四,在古代服饰研究史上,本书首次将元、明两代的服饰分门别类进行研究,系统探索其中的蒙古影响因子,充分体现跨朝代、长时段的研究突破。本书对古代服饰的研究强调多种史料互证,文字与图像并重。本书较之于传统工艺美术模式的古代服饰史研究,更加突出了历史文献的重要性。本书附录部分专门精选出有关的史料,这是以往服饰史著作所不具备的。而历史学者关于服饰的论述往往仅注重文献的引述,可能并不擅长图像史料的收集。
本书的现实意义也是非常突出的,这与一般的纯史学著作有所不同。如前所述,近年来古代服饰研究不断深入和得到热捧与年青一代中“汉服文化复兴”的社会现象有密切关联。因此本书的写作缘起,除了根植于学术思考,同时也含有现实关怀。那就是让本书的研究成果惠及当今“汉服热”风潮下的广大青年人,引导他们的思想,纠正他们的偏颇,实现学术与社会的良好互动,这是本书十分显著的现实意义。
三
和一般的著作不同,本书并没有把“绪论”而是将元明时人有关人们服饰中的“蒙古因素”的记载置于卷首,可以立即引发读者的关注,可谓别出心裁。略举两例:
况曳撒、大帽止宜用于行役,而非见君之服。(《明武宗实录》)
正德皇帝朱厚照之所以得到“武宗”的庙号,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尚武”。他在宫中喜欢和宦官、勇士中的高手过招,在边境喜欢找蒙古人切磋,所以多次率领京军、边军与蒙古鞑靼人角逐,并自称亲手格杀了一个蒙古骑士;听说江西宁王谋反,他立即率领大军南下,要与宁王在鄱阳湖决战。所以,尽管文官们说“曳撒、大帽止宜用于行役,而非见君之服”,但武宗却认为,只有以这样的服饰迎接,才能显示出自己“总督军务威武大将军总兵官”的身份。
今通用者又有陈子衣、阳明巾,此固名儒法服无论矣,若细缝裤褶,自是虏人上马之衣,何故士绅用之以为庄服也?(《万历野获编》)
这里所谓的“陈子衣”,当是名儒陈继儒的服饰。陈继儒号眉公,所载头巾称“眉公巾”,所坐马桶称“眉公马桶”。而所谓的“阳明巾”,则是传说中王阳明所戴的头巾样式。可见明代服饰的多元化,既有名儒之服饰,又有“虏人”之戎装,各取所需。
民族的交融,从来不是所谓“落后”用武力征服“先进”、“先进”用文化改造“落后”那样绝对化,民族的交融、文化的融合是双向乃至多向的。蒙古人进入中原后,开始习惯定居与农业,习惯读书与科举,汉人同样崇拜蒙古人的尚武乃至斗狠,而蒙古“马上”服饰,正是尚武、斗狠的标志。
罗玮的这本书能够有上述建树与创新,应该和最近十多年来考古发现的层出不穷、文物图像出版的突飞猛进有关。大量文物图册和文物展览不断推出,为这一课题的深入研究提供了前所未有的考古与图像资料。虽然许多服饰分类未必非常准确,但还是提供了一个历史视角的推进。当然,无论从文献还是图像的收集,以及在此基础上进行的研究来看,本书应该还属“初探”的阶段,期望罗玮的继续深入和研究。
方志远
明史学者,江西师范大学教授,校学术委员会主任,国家社科基金历史学科评审组专家,中国史学会理事,中国明史学会首席顾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