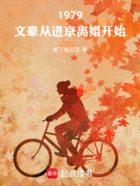
第20章 扎根
到了村口的老槐树下,两人分别。
孙安安往知青点方向去了。
陈阳转身往陈援朝家骑去。
陈援朝正在院子里劈柴,斧头抡得虎虎生风。
看见陈阳推车进来,他停下动作,抹了把汗:“回来啦?讲课怎么样?”
“还行吧。”陈阳把自行车靠在墙边,链条发出轻微的咔嗒声,“就是普通讲课。”
陈援朝把斧头插在木墩上:“少来!那可是县一中!快说说,啥感觉?”
陈阳无奈地笑笑:“真没什么特别的。就是台下人多了点,问题多了点……对了,谢谢你的自行车。”
陈援朝显然对这个平淡的回答不太满意:“你小子,现在可是名人了,还这么低调。
不过也是,你从小就这样,闷声干大事。”
闲扯了几句。
离开陈援朝家,陈阳慢慢往家走。
暮色四合,村里的炊烟袅袅升起,空气中飘荡着饭菜的香气。
几个放牛归来的孩童从他身边跑过,带起一阵欢快的笑声。
推开自家院门,陈芳正在井边洗菜,听见动静立刻抬起头:“哥!”
她甩了甩手上的水珠,“怎么样怎么样?讲课好玩吗?”
陈母从灶房探出头,围裙上沾着面粉:“回来啦?饭马上好。”
“挺好的。”陈阳把外套挂在门后的钉子上,“就是人多了点,有点吵。”
陈芳不依不饶地拽着他的袖子:“详细说说嘛!台下有多少人?他们都问你什么问题了?有记者采访你了吗?”
她连珠炮似的问题让陈阳哭笑不得。
“好好好,”陈阳举手投降,在院子里的凳子上坐下,“大概一百多人吧,问的最多的是高考作文怎么写……”
他简单讲了讲经过,省略了喝酒的部分。
陈芳托着腮帮子,眼睛亮晶晶的:“真厉害……我要是也能站在讲台上讲课就好了。”
陈阳揉了揉她的头发:“你好好努力吧。”
晚饭时,陈老汉也问起讲课的事。
陈阳一边扒拉着碗里的小米饭,一边回答父亲的问题。
陈老汉听得很认真,不时点头,脸上的皱纹舒展开来,显得年轻了几分。
“阳娃,”吃完饭,陈老汉突然说,“你现在出息了,但别忘了根本。”
他指了指脚下的土地,“咱们老陈家祖祖辈辈都是农民,做人要踏实。”
陈阳郑重地点头:“爹,我记下了。”
夜深了,陈阳躺在炕上,望着窗外的星星。
今天的经历像走马灯一样在脑海中回放。
讲台上专注的学生们,酒桌上热情的同事们,回家后陈芳的崇拜……
这一切都让他真切地感受到,自己已经在这个时代扎下了根。
远处传来几声犬吠,陈阳翻了个身,闭上眼睛。
明天还要去公社小学上课,高考也越来越近了。
……
公社小学的院子里,陈阳刚上完五年级的作文课,粉笔灰还沾在袖口上。
他推开教师办公室的木门,发出“吱呀”一声响。
办公室里空荡荡的,其他老师都去上课了。
他走到自己的位置坐下,从抽屉里取出高考复习资料,正准备继续钻研数学题,忽然听到一阵轻快的脚步声由远及近。
“陈老师,你在吗?”孙安安的声音从门外传来,带着几分期待和忐忑。
陈阳抬起头,看见孙安安站在门口,手里拿着一个牛皮纸袋,浅蓝色的确良衬衫衬得她肤色白皙,两条麻花辫垂在肩头。
“孙老师,有事吗?”陈阳合上书本,示意她进来。
孙安安快步走进办公室,将纸袋放在陈阳面前的桌上,动作轻柔却掩饰不住兴奋:“我把《春到陕北》修改好了,想请你再看看。”
陈阳接过纸袋,抽出里面的稿纸,纸张上密密麻麻写满了清秀的字迹,多处有修改的痕迹,但整体干净整洁。
“你改得很认真。”陈阳翻看着稿子,由衷地说。
孙安安拉过一把椅子坐在陈阳旁边,距离恰到好处——既不会太近显得冒昧,又不至于太远影响交流。
她双手交叠放在膝上,背挺得笔直,眼睛却忍不住往稿纸上瞟,像等待老师批改作业的学生,却忘了她才是正经老师。
“我按照你说的,把春耕那段提到了前面,”孙安安指着稿子的一处,“还有山桃花的描写也改得更具体了。”
陈阳顺着她指的地方看去,果然看到了全新的段落:
「山桃花开得正盛,粉白的花瓣在料峭春风中颤抖,像无数只欲飞未飞的蝶。走近了看,每朵花有五片花瓣,淡黄色的花蕊上沾着晨露,在阳光下闪闪发亮,宛如撒了一把碎金。」
“这个比喻很好。”陈阳点点头,嘴角微微上扬,“比原来的漫山遍野生动多了。”
孙安安的眼睛亮了起来:“真的吗?我改了好几次都不满意,最后是看到学校后山那片桃花才有的灵感。”
陈阳继续往下看,发现整篇文章的结构更加合理,细节描写也更加丰富。
孙安安不仅修正了他指出的问题,还增添了几处令人眼前一亮的描写。
“你进步很大。”陈阳放下稿子,真诚地说,“这样投出去,中的几率很大。”
孙安安双手不自觉地绞在一起:“真的可以投稿了吗?我还担心改得不够好……”
“文学创作没有完美,只有不断接近完美。”陈阳想起前世读过的一位作家的话,“你这篇已经很成熟了,可以尝试投稿了。”
孙安安深吸一口气,鼓起勇气问:“那……你觉得投哪里合适?”
陈阳思索片刻:“《燕京文艺》不错,他们喜欢这类描写地方风情的散文,而且稿费也相对丰厚。”
“《燕京文艺》?”孙安安惊呼出声,随即意识到自己失态,连忙压低声音,“那可是大刊物,我……我能行吗?”
陈阳看着她因紧张而微微颤动的睫毛,语气更加温和:“不试试怎么知道?我当初投《人民文学》时也没把握。”
他撒了个善意的谎言,实则投稿时就有了七八成过稿的把握。
孙安安咬了咬下唇,犹豫又渴望。
“好,我试试。”
最终,孙安安下定决心,“最坏不过是被退稿,反正也不是第一次了。”
陈阳笑了:“这才对。投稿地址我可以帮你查,信封和邮票准备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