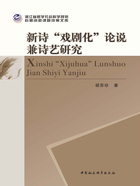
二 研究现状
从现有研究看来,学者一般注重单个诗人、诗家的“戏剧化”主张或某一诗群的戏剧化创作,现代时期的关注点普遍为袁可嘉的“新诗戏剧化”理论,卞之琳、穆旦的戏剧化手法,当代时期的研究基本是枝节性阐释张枣、翟永明、朱朱的戏剧化文本,具体如下。
由于袁可嘉在20世纪40年代将戏剧化和“新诗现代化”直接对应起来,加上他在当代对外国文学研究的引领和推动,他的“新诗戏剧化”理论相应成为最大的关注点。一些现代诗学集合性研究专著,普遍对袁可嘉的“新诗戏剧化”理论作专节介绍,如龙泉明、邹建军的《现代诗学》(2000),潘颂德的《中国现代新诗理论批评史》(2002),重点展述袁可嘉的戏剧主义诗学观,包括“客观性”“间接性”“客观对应物”“矛盾戏剧地展开”,前者还将“戏剧化”阐释为“经验中的戏剧性”,即“强调情节性和生活原生态保存”[15]。其他论述现代诗潮或专题性研究的专著也绕不开“戏剧化”,如孙玉石的《中国现代主义诗潮史论》(1999),龙泉明的《中国新诗流变论》(1999)、《中国新诗的现代性》(2005),蓝棣之的《现代诗的情感与形式》(2002),李怡的《中国现代新诗与古典诗歌传统》(1994),陈旭光的《中西诗学的会通——20世纪中国现代主义诗学研究》(2002),不同程度地论述了袁可嘉的戏剧化诗学观念,兼及卞之琳、穆旦诗歌文本的戏剧化手法,诸如戏剧化角色、戏剧性场景。蓝棣之在专著中还指出了新月诗人的戏剧化手法与维多利亚诗风的关系。这些论述逐渐成为关于现代时期新诗“戏剧化”的基本认识,专著之间的相关观点具有延续性、承继性关系。诗派研究专著方面,游友基的《九叶诗派研究》(1997),蒋登科的《九叶诗派的合璧艺术》(2002)、《九叶诗人论稿》(2006),马永波的《九叶诗派与西方现代主义》(2010),都论及了九叶诗人的“戏剧化”。还有个体诗人诗艺解读专著,如香港张曼仪的《卞之琳著译研究》(1989),江弱水的《卞之琳诗艺研究》(2000),对卞之琳复杂细腻的戏剧化角色和人称作了专业阐释,后者展开得更为全面而深入。此外,王毅结合徐志摩、闻一多个别诗篇提出新诗中“戏剧独白”形式的发展问题[16];刘燕则论析了艾略特对穆旦戏剧性场景和戏剧化角色的影响[17]。
在另一些研究当中,学者对所涉及的现代时期的“戏剧化”内涵作了更个人化的理解。如臧棣论述袁可嘉“现代化”诗学时,就发现了其背后的英美新批评中的“戏剧性”和综合矛盾、冲突的“包含性”的逻辑关系[18];蓝棣之也论及袁可嘉“戏剧化”诗学的具体西方来源[19]。对于袁可嘉的理论背景,一直专攻新批评诗学的学者赵毅衡,认为新批评的“戏剧化”意指将抒情文学“看作一出戏,里面包含着戏剧结构”[20]。也有大胆质疑的,青年学者张松建在《现代诗的再出发——中国四十年代现代主义诗潮新探》中就提出,袁可嘉“戏剧主义”诗学具有夹生性,未能“语境化”[21],这的确是至今仍须面对又颇难辨析的疑障。较为特殊的是刘方喜一文,他认为九叶诗人的“戏剧化”、新月诗人的“声情化”和现代派的“意象化”,合成了现代诗歌史上针对白话诗本体特质的三种“功能性”建构[22]。他的古典诗学背景决定其对“声情”的重视,对“戏剧化”的阐释有个人建构意图。另外,陈卫从朗诵、表演层面上的“戏剧化”讨论闻一多诗歌的节奏[23],属于舞台表现的“戏剧化”观照。
相对有关现代时期新诗“戏剧化”的研究局面,当代诗歌中的“戏剧化”论说较少得到非诗人型研究者关注。90年代诗歌出现了不同于以往“意象”“象征”等诗学概念的新知识谱系,如热议许久的“叙事性”。杨匡汉甚至提出,这一阶段“诗学明显走在小说学、散文学的前面,并给予后者影响性的启迪”[24]。程光炜以系列文章阐释了诗人的“知识型构”,并提出“1990年代诗歌”[25]这一批评概念。除了诗人自身对个人“戏剧化”诗观的敞明,几位长期跟踪先锋诗歌的评论家对诗人们的戏剧化写作特征稍有论及。如程光炜在其主编的诗选集《岁月的遗照》序言中,概述了翟永明的“戏剧性”追求;陈超在《西川诗歌论》《翟永明诗歌论》[26]中分别点明了两人与叶芝相类的“面具”写作意识;唐晓渡的《谁是翟永明》提及了翟永明不同于英美新批评定义的“戏剧化”特征[27]。此外,余旸(余祖政)、颜炼军也先后提到了张枣个性化的“面具”意识[28]。周瓒则概要性地提出,臧棣、翟永明、西川、陈东东、钟鸣、张枣等人的戏剧化实践构成了“新诗中的戏剧性”[29]。再有,王昌忠在出版的博士论文中亦涉及了90年代诗歌中的“综合性”和“戏剧化手法”[30]。此外,奚密对于坚的《0档案》被编成戏剧上演做过文本异同分析[31],和其他“戏剧化”论说指涉关系不大。
要专门提及的是,张桃洲在《现代汉语的诗性空间》一书中,专节提出了20世纪40年代和90年代诗歌“戏剧化”的对应性,为打通现、当代诗歌研究隔膜提供了新的思路和范式。另外,香港的梁秉钧,台湾的余光中、张汉良和叶维廉,亦分别在单篇文章中探讨穆旦、痖弦、卞之琳等具体诗人的“戏剧化”构思[32],他们的研究话语及论述风格亦具有借鉴与参照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