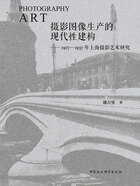
绪论
第一节 研究对象及选题缘由
一 研究对象
本书以1927—1937年的上海摄影艺术为研究对象,这里所谓的“摄影艺术”不同于中国摄影史语境中的“艺术摄影”。后者仅指涉那些由摄影家所创作的、以审美表现为目的的、非实用性的摄影作品,例如刘半农、郎静山、胡伯翔等人的“画意摄影”创作。我们可以将这个纯美学的概念视为狭义的“摄影艺术”,而与之相对应的“记录摄影”同时也可以被纳入广义的“摄影艺术”中,因为有些是以现实公用为目的的摄影,“艺术性可能不是摄影者当时的目的,但是时空改变后,摄影者的艺术涵养反而更凸显了”。[1]而且,具体到中国近代摄影艺术发展的语境中,可以发现当时的商业画报(《良友》《时代》《大众》等)所刊载的摄影作品如上海的建筑摄影、画报封面的人像摄影、民族志纪实摄影、体育新闻摄影等,以及图像编辑过程中出现的蒙太奇摄影设计本身就具有较强的艺术性,甚至有些还具有前卫性。显然,这些被排除在“艺术摄影”范畴之外的摄影创作和摄影设计极大地丰富了中国早期的摄影艺术。
况且“民国摄影的面向非常丰富,并非仅以艺术摄影而且主要是以业余摄影爱好者为主体的摄影创作可全面概括之”[2]。显然,若将“摄影艺术”狭隘地理解为“艺术摄影”,则会遮蔽掉近代中国摄影艺术的多重面向。所以,笔者以1927—1937年上海摄影艺术作为研究对象,取广义的“摄影艺术”概念,将所谓的“艺术摄影”和出现在画报与期刊中的、带有明显艺术特性的“记录摄影”均纳入研讨的视野范围之内。另外,第一章涉及对早期西方摄影师在中国的拍摄和本土照相馆的拍摄讨论,以及第三章中对早期照相馆摄影时代的摄影媒介观、摄影美学的论述,并非本书的重点,只是为了梳理出中国近代摄影艺术发展的线索和脉络,从而对1927—1937年的上海摄影艺术进行准确的定位。
若从摄影史的角度来看,本书需要关注的是当时出现在上海的摄影家(如郎静山、胡伯翔、金石声、陈传霖、聂光地等)及其摄影创作、主要的摄影团体(如“华社”“黑白影社”等)及其主办的专业摄影期刊(《天鹏》《中华摄影杂志》《飞鹰》等)和摄影展览。另外,还需要特别关注的是被很多摄影史忽略或轻视的商业画报,尤其是《良友》《时代》《大众》《柯达杂志》等,因为这些画报杂志无论是对于纯美学式的“艺术摄影”还是对于处于萌芽状态的现代摄影,都起着重要的助推作用。
除此之外,本书并不局限于一般意义上的摄影史研究,而是在梳理和总结1927—1937年上海摄影艺术发展状况的基础上,考掘推进其发展的话语机制及其背后的观念变迁。在艺术理论的层面上,探讨摄影在当时中国历史文化语境中,如何从图像记录的媒介工具到被广泛地接受为一门独立现代的视觉艺术,即摄影作为艺术门类的自我确证问题,并对此过程中产生的理论形态进行总结和提炼。再则,摄影艺术不仅是作为一种孤立无援的艺术创作而存在,同时它更是作为一种图像生产方式参与到了当时的精英启蒙文化、现代都市文化以及政治意识形态观念的建构之中,实现了中国摄影文化的现代性建构。本书还将以文化研究的视野对当时上海丰富多彩的摄影文化进行考察,打破现有研究中摄影本位主义的视野瓶颈,从而对十年繁荣期的上海摄影艺术进行更加全面而深入的定位和研究。
二 选题缘由
本书对中国摄影艺术的研究限定在1927—1937年的上海这个特定的时空范围内,首先是因为“从1927年至1937年,南北的统一为中国争取了难得的十年较为稳定发展时期。而这一时期也是中国历史上中外文化交流最多的时期”[3],此时的上海作为中国最为开放和现代化的大都市,必然成为中外文化交流最为集中的地方。再加上“1926年到1927年,北京在军阀的统治下,动荡和暴力事件不断,京城的作家和知识分子纷纷迁往上海的租界里居住……1937年因日本侵华导致新的移民潮和上海文艺团体外移,文化精英聚集上海的现象才告终止”[4],在这些南迁的文艺精英中就有享誉摄影界的“光社”核心成员陈万里、黄振玉等。可以说,作为摄影艺术发展的外部语境,政治的统一以及由此而带动的频繁的中外文化交流和本土文化中心的南移,无疑都为上海摄影艺术的繁荣提供了便利,也为中国摄影的第一个黄金时代作好了准备。
其次,除了政治因素提供的便利外,摄影艺术在1927—1937年的繁荣还与当时发生在上海的艺术事件,以及在上海成立的摄影团体也密切相关。具有标志性的艺术事件是“上海美术专科学校的‘天马会’于1927年举办第八届美术展览,特辟摄影部展出摄影作品,陈万里和郎静山等都送摄影作品参加展出。在展出期间他们交流了北京和上海摄影活动的情况,开始酝酿在上海组织摄影团体,举办摄影展览”[5]。“天马会”作为当时中国最具先锋性的美术团体,集中了刘海粟、汪亚尘、丁悚等著名的艺术家,影响力巨大。此次艺展对于摄影艺术发展的意义在于:一提升了摄影在现代艺术中的地位;二为南北摄影艺术家的沟通搭建了平台,陈万里和郎静山的碰面直接促成了1928年初“中华摄影学社”(简称“华社”)的成立。
“华社”的成立对于上海摄影艺术乃至中国摄影艺术的发展都有着标志性的意义,它在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一度成为“艺术摄影的代名词”[6],而且影响带动了一大批摄影艺术团体的成立,如复旦摄影学会、“黑白影社”等。“华社”之后的“黑白影社”“与华社一样拥有大规模公关运作能力……1930年元月成立之后,它很快成为民国时期会员最多、分布最广的摄影社团”[7]。如果说“华社”将中国的“画意摄影”推向了高潮,那么“黑白影社”则开启了对中国现代摄影的探索。可以说,二三十年代的上海摄影界先后集中了最具影响力的两个社团,它们均举办过具有全国影响力的摄影展览并创办了专业性较强的摄影期刊,极大地推进了我国摄影艺术的发展。
最后,此时段的上海拥有全国最为发达的大众传播体系,这对于摄影艺术的发展而言至关重要,它为摄影艺术的探索和普及提供了有力的支持。其中和摄影艺术发展相关的刊物主要可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商业性的综合性画报(含报纸的副刊),如《良友》《时代》《大众》等画报;另一类是专业性的摄影期刊,后者还可细分为由摄影商行出版的商业性的期刊(如《柯达杂志》《长虹》等),和由业余摄影家主办的艺术刊物(如《中华摄影杂志》《黑白影集》等),当然还有介于二者之间的由摄影商行赞助出版的,但是由业余摄影家主编的《飞鹰》杂志等。
这两类刊物对于摄影艺术的发展均起到了不可忽视的助推作用,只是它们所起到的作用各有侧重,综合性的商业画报在摄影艺术的多面向探索方面贡献要大于专业摄影期刊。因为前者以其庞大的发行优势和读者群成为当时大众传媒的重心所在,“更成为传媒中最主要的图像传播媒介。在摄影与传播媒介的紧密关系中,艺术摄影被视为现代中国艺术之一,并得到特殊的关照”[8],很多画报都开辟有“艺术摄影”的专栏,刊载了如郎静山、胡伯翔、陈传霖等人的“画意摄影”以及陈嘉震、陈昺德、王钰槐、敖恩洪等人的现代主义摄影。并且这些画报还凭借着对西方摄影潮流的跟进和沟通优势,意外地创作了一定数量的前卫的摄影作品,如中国最早的蒙太奇摄影就出现在《良友》《时代》《大众》画报中。
而摄影期刊的贡献则侧重于推介普及专业摄影知识和探索建构摄影理论方面。很多重要的摄影批评和理论文章均发表在当时上海出版的摄影期刊中,其中包括很多非上海摄影家的重要理论文章,如北京张印泉的《现代美术摄影的趋势》和南京影社王洁之的《绘画与摄影》《像与不像》分别发表在上海“华社”主办的《中华摄影杂志》和“鹰社”主编的《飞鹰》上。这些充分说明了当时上海已然成为了中国摄影艺术发展的核心重镇。
由上述三点可以看出,1927—1937年的上海摄影艺术在中国摄影史中的地位非同一般,然而目前国内学界对其关注还远远不够,并且在现有的很多研究中还经常会因为对相关概念的混用和误视,而遮蔽了许多具有重大学术价值的研究对象。更严重的是因为这些研究的缺失甚至空白而出现了许多亟须肃清的误区,如很多人认为当时中国摄影艺术中并没有出现类似于西方的现代主义摄影,显然这是由于他们对当时的“画意摄影”“艺术摄影”“美术摄影”等概念之间的混用产生了误解。“画意摄影”在当时的摄影语境中意味着宽泛意义上的“艺术摄影”或“美术摄影”,甚至可以将处于萌芽状态的现代摄影纳入其中。然而很多研究者却误以为“画意摄影”仅指那些模仿传统文人画或西方印象画的艺术创作,结果就因为这种概念上的误解而使他们忽视了“黑白影社”对我国现代摄影的探索和努力。[9]
而目前学界对《大众》《时代》等综合性商业画报研究的不足或缺失,则使得现有的中国摄影史研究错失了许多精彩的内容。这些商业画报不仅展现了相当数量的“画意摄影”和“现代摄影”,而且其中还包含了一定数量的前卫摄影作品。虽然这些前卫性的摄影作品来自画报编辑的美术设计,但是我们却不能无视它们在视觉艺术中的突破和贡献:大胆的形式实验和鲜活的感性开拓。
以上这些研究的不足和缺失必然导致不能全面而深入地了解此时期上海摄影艺术的发展样态,同时还会掣肘对摄影理论的总结和提炼,比如现有的摄影研究就摄影如何在特定的中国历史语境中实现其艺术身份的合法确证问题的探讨,仍存在很大的不足。如果缺少了对现代摄影的考掘和总结,就无法对此摄影理论的基本问题开展研究。研究的不足同时也意味着该领域可待发掘和整理的问题大量存在,这也是笔者选取1927—1937年上海摄影艺术作为研究对象的一个重要原因。
此外,从摄影本位主义的视野出发,我们发现此时段上海摄影艺术的地位如此重要,但是对此的研究却严重不足。同样若跳脱出这种相对狭隘的摄影本位主义,从文化研究的视野去打量此时期的上海摄影艺术,将会开拓出更为宽泛的学术空间。然而目前类似这样的研究也是严重缺失或不足,“鉴于摄影在民国时期的发展以及视觉文化上的影响,相关研究对于中国摄影探讨的缺乏确实令人惊奇的。近年来许多中国研究探讨了民国时期的电影、海报、漫画及画报,但摄影对这些视觉媒体中的基本元素却缺乏关注”[10]。摄影在当时上海视觉文化中的作用并非局限于精英阶层自娱式的美学创作,同时更是作为一种图像生产方式建构着我国视觉文化的现代性。这些既是笔者选题的缘由,同时也是研究突破的方向和可供选择的进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