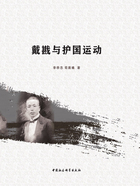
二 留学东瀛
光绪三十一年(1905)[15],虚龄已经二十六岁的戴戡获得公派留学机会,从而迎来了人生中的一次重大转折。作为一名来自西南边陲、出身寒微的普通士子,戴戡得以迅速跻身于全国性的士人精英网络,并且站在了时代潮流的前端。
这年正月,戴戡得到恩师郎先锦帮助,偕同郎师长子郎治香前往省城贵阳,一起投入比自己稍长几岁的徐天叙门下。徐天叙(字淑一)也是贵定人,出身于贵阳学古书院(经世学堂),戊戌维新前后曾经直接受教于著名改革派学者严修门下,同学当中有熊范舆、姚华、刘显治、周恭寿、黄禄贞、唐桂馨、陈廷棻、张协陆、钟昌祚等人。[16]进入20世纪,这批人开始活跃于政治、文化等领域,逐渐成为贵州乃至全国舞台上的风云人物。1901年,徐天叙在贵州乡试中考取举人,1903年继姚华、熊范舆之后担任兴义笔山书院山长,后来又与友人在贵阳创办时敏学堂。1905年秋,徐天叙与在籍内阁中书唐尔镛、任可澄等人联名呈请贵州巡抚林绍年,建议将省城贡院改组为师范传习所,以培养全省师资。[17]通过这些办学活动,徐天叙逐渐成为贵州文化教育领域的知名人士,在政、学两界均有较高声望。戴戡从旧治小城来到全省的政治、文化中心,直接进入徐天叙的圈子,环境和机遇都发生了很大变化。在这里,他不仅可以结交省内其他地方的优秀青年学人,还可通过师友的知识结构和人际网络,接触到更加丰富的信息,以及贵州以外更加广阔的世界。
甲午战争以后,原先沉醉在“天朝上国”美梦中的士大夫精英顿感错愕与震惊,随之兴起一股赴日留学/游学的新潮流。1896年,清政府派出第一批留日学生共13人,此为中国近代留日运动之嚆矢。[18]进入20世纪之后,留日学生逐年增多。不过贵州僻处西南腹地,当时对外交通极为不便,留日潮流一开始并未在黔省产生多大影响。根据清政府的统一要求,1904年贵州应该选送3名留学生,结果竟然无人派出。[19]
1904年冬,云南巡抚林绍年(1846—1916)调署贵州巡抚。鉴于西南地区师资缺乏、学堂不兴、学务不振,他到任后力推留学工作,将之作为头等大事来抓。林绍年要求各州县就地筹款,每县至少资送速成师范科留学生1—2人,如果地方财力允许,则另外资送专门科留学生1—2人,并要求留学生毕业回国后先在本省服务。在林绍年大力推动下,选派留学工作取得了非常明显的进展。1905年春、夏两季,全省各县共选出64人,分别于农历三、四、五、七月派往日本。[20]此后,这项工作在秋冬两季继续进行,截至1905年年底,贵州全省一共派出150名留学生,其中官费/公费112人、自费38人,以入读一年制速成师范科者居多(见表1—1)。
表1-1 1905年贵州派出留日学生名单

表1-1 1905年贵州派出留日学生名单续表

资料来源:《选派学生出洋折》(光绪三十一年七月)、《高等学堂设立预备科并派员出洋考察折》(光绪三十一年十月)、《黔省秋冬两季咨送学生出洋片》(光绪三十一年十二月),均收入林葆恒编《闽县林侍郎(绍年)奏稿》卷四《抚黔奏稿》,第16—17、43、66页(台湾文海出版社1969年影印版,第467—470、522、567—568页)。
林绍年发起的留日学生选派工作,在各县实施起来并不容易。一方面,贵州经济普遍落后,各县财政大都较为困难,留学经费不容易筹措,有的地方找到了合适的留学人选,却没有钱;另一方面,当时贵州留学风气未开,许多人并不关注此事,人才尤其匮乏,有的地方好不容易筹到了钱,却找不到合适的人选。[21]在这种情况下,一些有眼光、有名望的士绅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们敏锐地意识到了这件事的重要性,积极推荐熟悉的人才,努力争取官绅的支持,这样既帮助地方官员完成了上级交派的选送任务,也帮助自己的门生子弟获得了新的成长机会。
戴戡来到省城之际,公派留学选拔工作正好刚刚开始。借助于两位老师的声望,特别是徐天叙的影响力,戴戡在贵定县的选拔中独占优势。他以县学廪生身份获得首批公派资格,迎来了自己人生中难得的一次机会。当时,他使用的仍然是原名“戴登荣”[22]。值得注意的是,与戴戡同赴贵阳、朝夕相处的郎治香却没能获选,而是进入徐天叙倡设的师范传习所学习。这表明郎先锦以人才为重,因材施教,并没有对自己的儿子特别偏袒。贵定县首批获选的另一人是朱俊龙,亦为廪生。戴、朱两人不仅在贵定县,即便在贵州全省,也算得上外出留学的先驱。民国时期编纂的《贵定县志稿》记载说:“戴、朱诸君就学东瀛,先于他县。士习有所观摩,咸知奋起。”[23]
戴戡是在1905年春夏之间派出的。[24]抵达日本后,他与贵州籍以及来自其他一些省份的留学生一样,进入东京的宏文学院,学习一年制速成师范科。这是一所专为接收中国留学生而开设的学校,创办人是东京高等师范学校校长嘉纳治五郎,原名亦乐书院,1902年更名为弘文书院,后因“弘文”与清朝乾隆皇帝“弘历”的名讳冲突,引发旗人身份的中国留学生不满,又改名为“宏文书院”。针对中国留学生的需要,宏文学院主要采取速成教育模式,而且学制灵活,从6个月至1年半不等,此外也有学制三年的普通科。到1906年10月底,从宏文学院毕业的中国学生已有1959人,在读生1615人。黄兴、鲁迅、陈独秀赴日之初都在该校学习过。至1909年关闭时,这所学校总共接收了中国学生7192人,毕业生3810人。[25]
1906年夏秋之间,戴戡完成了一年制速成师范科的学习,决定延期一年,转而攻读高等理化科[26],学习采矿冶金方面的知识。[27]然而根据原来的派遣方案,他所获公费资助仅有一年。延期一年所需经费,则需再行筹措。为此,他在两个学年的间隙回了一趟家乡,一是看望家人,二是向郎师汇报学习情况,并寻求再次资助。[28]这一次,恩师郎先锦又提供了有力的帮助。
戴戡留学经费的落实,很大程度上得益于相沿已久的文庙学田。以往论著说他的留学经费出自贵定“六庙”庙产,均不确切。文庙是孔庙的别称,明清时期每个县级行政单位都有一座文庙,作为辖区内的祭孔场所和文教中心。很多地方的文庙往往还有自己的学田,也就是农业时代的地方公共文教基金。贵定县府迁走之后,旧治文庙虽已失去正祀资格,但它仍然作为地方文教机构而存在。根据道光时期文献记载,旧治文庙拥有东门外、高家寨、界牌、大学坡、谷壤坝、左九6 处学田(包括旱地),合计60.1594 亩,此外还有4处廪田。由于部分田土荒芜,旧治文庙学田实际出租的大约35亩,每年租谷收入将近40 石。贵定县文庙的学田规模更大,合计30处192亩,实际出租的大约80亩,不过租金较低,每年租谷收入只有16石;此外还有5 处廪田,以及牛胙田、羊胙田、鸡鸭田、菜苗田、香灯田等。文庙学田的租谷收入(民间俗称庙谷)纳入全县统筹,用于资助当地贫寒学子。[29]到了清末,旧治文庙和贵定县文庙的学田依然在发挥作用。省里要求各县自行筹款选派公费留学生,各地的文庙学田收入自然是现成的资源。特别是戴戡第二年的留学,并不在原定公费资助之列。但郎先锦积极游说地方士绅,盛赞戴戡“敏而好学,德才兼备,前程远大”,“吾辈有责为国育才”,提议变卖庙谷资助戴戡留学。在郎师鼎力帮助下,据说戴戡先后获得四百两纹银。[30]当时1两银子大致相当于银元1.4元,银元与日元的比价则大体持平。[31]宏文书院的学费加住宿费,一年需要300日元。[32]以此推算,文庙学田所能提供的经费,对于戴戡的留学所需而言还是略显紧张。
留学经历的收获不仅在于知识方面,日常生活中潜移默化的影响也很重要。日本社会的文明开化气息,往往给第一代留日学生留下深刻印象。例如,看到日本各地遍设学校、人民普遍接受教育,中国留学生不禁感叹:“日本学校之多,如我国之鸦片烟馆。其学生之众,如我国之染烟瘾者。”[33]就连一些日常生活中的细节,也让他们受到触动。当时有一本书名为《留学生自治要训》,在他们当中颇为流行,其中讲了很多具体的经验。比如:衣服要清洁;室内要打扫干净;不可随地吐痰;痰要吐在痰盂里;不可随地小便;大小便要排在便器中;入浴之际,先把下半身洗干净,才可进入浴池里;同住者写信时或温习时,不要在旁打扰;他人书桌上的书籍或抽屉中的物件,不可乱翻;就寝时要熄灯;夜间不要大声呼叫;对下女(相当于女佣)要庄重,不可开玩笑;往来道路须靠左行;在路上遇见友人,不可高声呼唤,也不可久立路边闲聊,稍作倾谈,行过礼即宜分手;前往参观时,要认清出口、入口,不可大声谈话;电车满座之时,应让座与老人、小孩和妇人;电车内不可抽烟或盘腿而坐;等等。[34]这些经验貌似琐细,其实大有深意。二十年后,孙中山仍然指出,中国人虽然素来讲究修齐治平,但往往一举一动,极寻常的修身功夫都不讲究,“像吐痰、放屁、留长指甲、不洗牙齿,都是修身上寻常的功夫,中国人都不检点。所以我们虽然有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大知识,外国人一遇见了便以为很野蛮”[35]。为此,孙中山希望年轻人能够多学习外国人的生活文化,从修身认真做起,再讲齐家、治国,谋求中国的进步。孙中山这一观点和主张,乃是基于几十年的海外阅历有感而发。第一代留日学生的经历和体验,正好与孙中山的观点相互印证。
留日期间,戴戡与贵州同乡多有交往。当时在日本的一些贵州籍学生成立了时敏同志会,旨在团结互助,共策共进。该组织的成员,有人追随孙中山的激进革命路线,也有人追随梁启超的渐进立宪主张。随着孙、梁两派关系破裂并激起论战,时敏同志会的成员也分道扬镳。[36]戴戡参加了时敏同志会的活动,并留下了一张与秋瑾等人的珍贵合影。[37]

图4 戴戡与时敏同志会合影,1906年
(前排左三为秋瑾,时为中国留日学生组织负责人之一;中排左一为戴戡)
戴戡与立宪派人士的关系更加紧密。1906年秋,徐天叙前往日本考察学务,在东京待了一年左右,与在日本法政大学学习的蹇念益、陈国祥、熊范舆等旧日同窗相聚甚欢。由于老师徐天叙的原因,戴戡也跟他们成为好友。蹇念益(1876—1930),字季常,贵州遵义人,“庚子事变”之后游学日本,入早稻田大学学习法政,曾经担任留日学生会总干事,主张君主立宪,与立宪派精神领袖梁启超(1873—1929)成为知交。[38]陈国祥(1876—1921),字宝贤,号敬民[39],贵阳府修文县人,其父为光绪年间进士、翰林院庶吉士,他自己于1897 年考中举人,1903 年考取进士[40],次年赴日之后,与梁启超关系密切。

图5 戴戡与贵州籍留日学生合影
(前排左三为戴戡,后排左二为徐天叙。徐天叙比戴戡晚一年赴日,此时戴戡已在留日学生中崭露头角,气度俨然超乎老师徐天叙之上)

图6 戴戡密友熊范舆留日期间肖像
(熊范舆长孙熊温礼先生据熊范舆早年照片用铅笔临摹而成,2011年1月翻拍)
戴戡与熊范舆的关系尤为密切。熊范舆(1878—1920),本名继先,字承之,号铁岩,贵阳府贵筑县人,早年在贵阳学古书院(经世学堂)学习时与徐天叙是同窗好友。1904年,熊范舆考中最后一科进士,随即前往日本,留日期间与梁启超、杨度等人交好,在东京发起成立宪政讲习会,被公举为会长,并且创办《中国新报》,与梁启超相互呼应,一同提倡立宪运动。[41]熊、戴二人经由徐天叙介绍之后,逐渐成为莫逆之交,后来还结成“扁担亲”:戴戡长子戴汝愚娶熊范舆长女熊菊英为妻,戴戡之女戴慧贞则嫁给熊范舆幼子熊其仁。又可能是由于戴戡的因素,熊范舆又与戴戡的恩师郎先锦成为儿女亲家,郎先锦次女郎淑贞嫁给了熊范舆长子熊其锐。[42]
受蹇念益、陈国祥、熊范舆等人影响,戴戡接受了渐进式立宪救国的思想,并与梁启超建立了密切联系。1907 年10 月梁启超在东京组织政闻社,蹇念益、陈国祥、戴戡都加入其中,并成为骨干。政闻社有四条纲领:第一,实行国会制度,建设责任政府;第二,厘定法律,巩固司法权之独立;第三,确立地方自治,正中央、地方之权限;第四,慎重外交,保持对等权利。政闻社的核心任务是,动员全国民众发起请愿运动,立即召开国会,改选政府。为了打消清政府的疑虑,梁启超在《政闻社宣言书》中郑重宣告:“政闻社所执之方法,常以秩序的行动,为正当之要求。其对于皇室,绝无干犯尊严之心;其对于国家,绝无扰紊治安之举。”[43]1908年2月,政闻社总部迁往上海,随后开始广泛联络国内立宪团体,发起国会请愿运动。但这种和平的立宪运动仍然为清政府所忌,1908年8月,清政府下令将政闻社查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