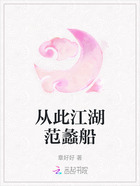
第4章
次日清早,张浥晨跟程霏霏在巷子口的杭州小笼包吃过早饭,又亲昵地拥抱了一会儿,接着张浥晨去上班,程霏霏去海淀区面试。她去面的是一家知名的互联网门户网站,作为一名应届毕业生,她的简历上除了工作热情态度积极以外乏善可陈。虚度的读书时光让她有些叶公好龙,向往好的机会,来了又很怕。
程霏霏下了公交车,沿着来之前查好的路线走,不知道是紧张还是因为天生路痴,不过一刻钟她就迷了路。问了路人甲,对方摇摇头,问了路人乙,同样摇摇头。她左顾右盼,在北京竟难遇到一个北京人。摸了半天路,她朝着一个看似正确的方向跑,发现错了,又朝反方向加速跑,心中骂自己是笨蛋。东跑西颠,总算摸进了写字楼,此时已迟到两分钟。只见玻璃门紧锁,前台像是被拉长了焦距,远远地站在办公区里侧,带着工牌的同龄人穿梭其中。
程霏霏给面试官打电话,对方冷冷地说道:“您不用进来了。我们有规定,迟到者一律取消面试资格。”她连忙解释,才刚到北京人生地不熟,对方又说:“更不考虑连面试地点都找不到的人。”
程霏霏吹了吹眉毛,只好转身,刚想给张浥晨打电话诉苦,又把手机放了回去——这么丢脸的事可不能让张浥晨知道。
她信步溜达,撞见了中关村图书大厦,正好进去消磨时光。她在班得瑞的背景音乐里凝神静气,逐渐忘记了刚才的不快。快离开书城时,买了一本精装版《月亮与六便士》。
程霏霏回到中滩村。中关村和中滩村,一字之差,天壤之别。她在巷子岔路左转,转进一个菜市场。菜贩子卖菜收了钱朝身后的纸盒子扔,手法稳准狠。一干人簇拥着挑拣廉价的新鲜芒果,夕照之中的菜市场一派热闹。地面上有一些被丢弃的蔬菜叶,鱼贩子扔掉的鱼鳞片,不时有难闻的气味扑鼻而来。程霏霏缺乏耐心,速战速决地买好了食材和调味,想到可以在张浥晨面前大显身手,竟有几分期待,不自觉哼唱起了那首《北京欢迎你》。
张浥晨推门时,程霏霏刚好打开电饭锅,让他闻到了米香。麻辣基围虾盛到了简单的白色瓷盘中,红通通的,显得格外好吃。两人一起把碗筷摆到两公分高的小桌上,席地而坐,吃得津津有味。
张浥晨对程霏霏说:“下午想问问你面试怎么样了,给你打了两个电话都没接。你的电话不要静音”。他说着拿过她的手机改成了响铃模式,随即试拨了一下,生涩坚硬的铃声响了几下。程霏霏才说:“我下午有点忙,没看手机。”
张浥晨见女友一字不提面试的经过,猜她不太顺利。北京人才济济,一蹴而就的事本就不多。于是他提议周末去中关村逛街。程霏霏把碗擦干,放好,转身问他:“去哪儿?”
“金海商厦”。
程霏霏听到这名字直皱眉,就是她才去面试的地方。
“怎么啦?”
“啊?没,没事没事。”程霏霏故作潇洒,假笑着。张浥晨见她表情可爱,弯起食指刮她小巧的鼻子,顺势拥着她靠在床上,不停亲吻她。程霏霏以为他只是玩闹,笑着反抗:“还要忙正事,简历没写完。”他按住她不肯放:“等会儿再写,这才是正事”。程霏霏说他这是“饱暖思淫欲”,但身体很诚实,她喜欢与他肌肤相亲的感觉以及他头发上妮维雅洗发水味道。
周六,张浥晨休息,和程霏霏去逛街。一进金海商厦的正门,样貌年轻身材清瘦的男销售员就笑意盈盈地迎上来,殷勤热络:“两位好!看看手机?去哪儿啊?用不用指个路?”虽然路人通通不予理睬,销售员们照样高高兴兴,朝着摸不着方向的人高声说:“电梯在内边儿!洗手间在内边儿!”程霏霏不解地看着他们,看起来那么快乐,好像有使不完的劲儿。他们在小家电区域逛了一会儿又去看手机,是三星、诺基亚、摩托罗拉这些牌子。一部带着“世界风Anycall”标识的新手机被放在了柜台中央。操着东北口音的销售员正向两个中年男人介绍着:哥,这款三星W579,最新款翻盖设计,像素贼高,500万像素,待机两天没问题……
张浥晨独自在一旁看诺基亚,看中了一款银色的N95。他想要买给程霏霏。程霏霏看到折后的价格都要6200,还要固定一项话费套餐,拉着张浥晨就要走:“疯了吧?买这么贵的手机,不要不要。”
张浥晨却不以为然。“拿这样的手机在街上走,你谁也不用怕。”程霏霏不接纳这个理由:“路上又没有黑社会。再说,这是手机,又不是手枪。你笑死我了。”她说完仍然拉着张浥晨离开柜台。张浥晨又把程霏霏拉了回来,圈在臂弯里:“我知道你喜欢白色,但这款银色的也适合女生用,你喜欢吗?”
程霏霏在张浥晨臂弯里觉得温暖而平静,点点头。张浥晨行事极稳重,买手机是个大开销,要稳妥,最好是找认识的人。“刚巧有一个同乡在这里卖数码,我找他帮着把把关。”张浥晨在电话里用方言交流,没一会儿一个叫王刚的男生就来了。他在这里卖学习机一类的产品,对手机销售的情况多懂一些。他告诉张浥晨查电子串号就能检验出手机是行货还是水货。又说,好的水货也不影响使用,坏了哪里都能修。王刚拿着那款诺基亚N95,里外连同包装都细看了一遍,告诉张浥晨放心买。不知不觉时间到了中午,三人到商场里的吉野家吃饭。
餐桌上,张浥晨略带得意地把手机递给程霏霏:给你壮壮胆,以后谁也不用怕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