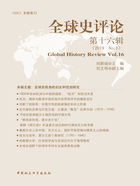
引言 中国与欧洲的国家建设进程和家庭动力
本文旨在从比较视角探讨18世纪末19世纪初中国与欧洲国家建设的逻辑,重点探讨国家政策对家庭经济关系特别是对性别分工的影响。我们建议对欧洲和中国的国家战略和可能影响家庭的统治思想(包括家庭战略和经济生存的可能性、劳动分配、性别和代际关系)进行对比。[1]首先,我们简要比较在漫长的18世纪中国和欧洲相关的一些国家建设进程。尽管本文对欧洲和中国的国家目标和战略没有进行详细的介绍,但我们仍希望对影响国家经济关系的规则逻辑进行一些总体比较。
有证据表明,清朝皇帝及其官员仍受一些传统儒家信条的影响。邓海伦(Helen Dunstan)指出:“在前现代中国,支持大众生存的政府行为在意识形态上仍以对大众福祉负责的儒家学说为前提。”然而,她又提出:“在乾隆初年,关于市场功能和国家介入其中的影响,核心论据都是技术和经济方面的,而不是儒家思想。”[2]不过,大多数历史学家都认为,中国的国家政策较多着眼于维护社会稳定,而不是鼓励财政收益或增长。苏珊·曼恩(Susan Mann)曾援引1727年一项建议重视粮食生产的谕令:
朕观四民之业,士之外,农为最贵。凡士工商贾,皆赖食于农,故农为天下之本务,而工贾皆其末也。今若欲于器用服玩之物,争尚华巧,必将多用工匠。市肆之中,多一工作之人,即田亩之中少一耕稼之人,且愚民见工匠之利,多于力田,必群趋而为工;群趋为工,则物之制造者必多,物多,则售卖不易,必至壅滞而价贱。是逐末之人多,不但有害于农,而并有害于工也。[3]
理查德·冯·格莱恩(Richard Von Glahn)认为,清政府是最小限度的干涉主义者,可将其最为恰当地描述为“一个供给国,一个通过投入饥荒救济和防洪而致力于改善民生的国家”[4]。这与邓海伦强调建立公共粮仓以稳定粮食供应的主张[她引用了罗威廉(William Rowe)的提法]一致:“无论时空如何转变,清政府都能对粮食价格稳定作出制度性的承诺,这在当时世界任何地方都是无与伦比的,清朝下令其数千名县级官员在每年收成时购买廉价的粮食,并在春天以略低于当时规定的较高价格转卖。”[5]然而,冯·格莱恩也注意到,在漫长的18世纪,清政府策略发生了变化:“早在1748年,最杰出的政治家就曾表示,人口增长(这一直被视为治世的标志)超过粮食生产令人担忧,因为它会造成不平衡,粮食价格的提高会对国家的生存构成地方性的威胁……1750年后,清政府从维持大量的(粮食)储备转向为常平仓(ever-normal granary)管理者提供资金,让他们在公开市场上购买粮食。”[6]邓海伦同样指出:“相对而言,清政府从追求‘仁慈’的铺张行为转变为富有纪律性、更符合满族传统的黩武精神。”[7]尽管清政府正朝着以市场为导向的统治策略迈进,但冯·格莱恩同意王国斌的主张,即“清朝统治者在社会和经济福利问题上比同时期的欧洲人表现出更大的关注”[8]。
“相对仁慈”的主张确实取决于同时代欧洲国家建设过程中冷酷无情的本质。原则上来说,长期以来欧洲君主的统治策略建立在一个足够富裕的农民群体的基础上,这个群体能够从他们农场的农产品(主要是各种谷物)中纳税。但在近代早期,他们在不同程度上取得了成功,因为他们与贵族地主竞争,而贵族地主通常收取现金或实物租金,而不是与农奴制相关的旧劳役费。尽管结果因地区而异,国家建设者经常努力让自己融入乡村生活,以保护农民家庭免受地主的侵害。此外,以近代早期欧洲政治生活为特征的国家中心之间的激烈竞争,意味着税收负担越来越严重,许多统治者争相寻找其他收入和权力来源——包括新形式的公债——这实际上使他们越来越依赖金融资本。查尔斯·蒂利(Charles Tilly)对这一过程的总结反映出,几个世纪后它仍可能引起愤怒:“我们在愉快的回顾中称为‘国家形成’的东西,包括向农民征税而不利于贫穷的农民和工匠、为了交税被迫出卖本该用来支付嫁妆的牲畜、把当地首领囚禁起来作为人质以使当地社区支付欠税、绞死其他胆敢抗议者;放任残忍的士兵侵害不幸的市民;征召年轻人——他们曾是其父母安度晚年的慰藉;强迫购买污染的食盐;把已经趾高气扬的地方富豪提升为国家官员,以及以公共秩序和道德的名义强制推行宗教一致。”[9]
国家建设模式的对比依赖于不同的阶级联盟。联盟战略中的一些变化有助于解释欧洲各国相对于农村地区不同的国家抉择和政策。但我们的目的是指出欧洲和中国之间的一般差异。拉维·帕拉特(Ravi Palat)在以印度洋的比较全球史(comparative global history)为中心的分析中指出,与南亚等国和中国相比,欧洲国家在巩固权力,以及发动对成功至关重要的欧洲大陆和殖民地战争方面,越来越依赖于商业金融家。反过来,对金融家的依赖往往导致欧洲国家建设者作出让步,以鼓励资本积累。例如,正如下文我们将要进一步讨论的,一些近代早期的国家建设者向商人公司提供特许经营权和垄断权,使他们更有能力投资于农村工业或殖民地贸易,从而获得更大的利润。国家建设者和金融家的联合鼓励了商品化财产关系在其整个领域的扩展,从长远来看,这导致了在欧洲及其之外的殖民地不再关注维持生计的资源。[10]
当然,这种过度概括掩盖了多样性,欧洲和亚洲采取的国家建设战略自然有所不同。然而,帕拉特的总体主张是有说服力的,因为他和中国很多历史学家一样,强调亚洲某些地区有一种不依赖金融资本、反而植根于家庭经济变化的国家建设模式。具体地说,有证据表明,印度洋流域许多国家的经济战略,建立在高产水稻农业生态的基础上,与劳动者的劳动(尤其是致力于生产纺织品以补充家庭农业收入的妇女劳动)强度增加相结合,农业产量不断提高。[11]农业税是中国政府预算的主要支柱,到18世纪中叶,征税单位不再是家庭而是土地。根据1766年的文献记录:“土地税产生了近四分之三的国家收入。”此外,清政府甚至没有重新勘测土地,而是将土地税固定在1711年的额度。冯·格莱恩认为:“与前朝明朝一样,清朝仍采用儒家的最低税收标准,这就限制了它进行基础设施投资或提供公共福利的能力。”[12]
因此,与大多数欧洲主要国家相比,清政府并不依赖借贷或私下与商人进行交易。于尔根·柯卡(Jürgen Kocka)重申了这一对比:“支持欧洲资本主义的商人或至少是他们的主要代表,对政治施加了直接影响……相比之下,中国、阿拉伯和印度的商人,都被限制在权力的前厅,而且他们很少像欧洲那样为国家形成提供资金。”[13]但这并不意味着商人对清政府毫无用处。任以都(E-tu Zen Sun)描述了二者之间的各种关系,包括“招商”。[14]这是一种较受欢迎的互动方式,通过这种方式,清政府既可以招募商人投资和从事政府项目,如大规模进口铜或出口丝(显然并非总能收支相抵),财政部门又可以对商人进行严格审查,并时不时将他们聚集起来,但政府并不依赖商人。[15]
任何事物都并非一成不变。清政府的重要官员和理论家如陈宏谋(1696—1771)就非常重视商业。罗威廉(William Rowe)认为,“特别是在18世纪,商业社会和经济价值取得精英阶层的广泛认可,这是以前从没有过的”,这一观点对商人和商业价值有了新的认识。甚至在文献记载中他还有这样的建议:“减少粮仓储备是为了回应那些代表商业利益的官员们的请求,他们希望消除国家对私人贸易的竞争,乾隆皇帝接受了这一建议,因为他暗中希望把每年用于补充粮仓的资金转移到西部边境的军事冒险活动。”[16]但总有一些例外,如扬州的盐业垄断,清政府的基本预算和行政管理都不依赖商人。[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