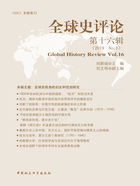
欧洲的国家经济发展与性别
现在我们将更直接地转向被称之为“经济”的国家政策。无论在近代早期的欧洲国家还是中国,决策者都把经济当作一个管理领域,并将其视为国家政治成功的关键因素。国家鼓励经济发展在欧洲和中国都是一个性别化的过程,但方式不同。在此,我们强调的是各种国家经济关系理论的假设,以及对家庭劳动和性别关系具有影响的新的经济发展计划,我们的重点放在国家参与纺织行业的比较分析上,主要集中于丝绸但亦不限于丝绸。
在欧洲,新的经济概念在国家行政领域得到了非常具体的阐述。马里恩·格雷(Marion Gray)追踪研究了在漫长的18世纪与“经济”相关的概念的演变,这些概念在德语文献报告和政治小册子中都有记载。他的调查始于17世纪,当时“经济不过和家庭(household)等同”。[18]在格雷研究的早期作品中,一对已婚夫妇——家庭主夫和家庭主妇(家庭之父和家庭之母)——共同掌管着家庭经济。经济建议更多地针对男性家长,因为整个家族事业都在他的终极权威之下。然而,他妻子的活动被认为是家庭成功的关键。在漫长的18世纪,这一切都发生了改变。随着经济转向市场,国家更多地参与经济管理,“经济”走出了家庭,变得越来越男性化,而女性做的家务则越来越被视为“没有生产力”。[19]
近代早期欧洲国家建设者把纺织品作为国家鼓励“经济发展”的重点。原始工业的发展模式与欧洲的家庭和人口制度密切相关,而且原始工业的政治层面随时可见。无论采取什么形式——贸易公司章程、保护性关税、禁止进口布料、对新产业的补贴,甚至是国有企业——国家对纺织品贸易的干预在整个欧洲都是显而易见的。近来全球史的发展表明,国家与企业之间的合作在欧洲经济发展中具有相对重要性,这种相互依存使得起初把“自由市场”作为欧洲工业化独特动力的观点变得更加复杂。[20]
就许多欧洲国家建设者的战略而言,羊毛、亚麻和丝绸工业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他们采用的都是在当地生产或至少能够在当地生产的农产品(绵羊的羊毛、亚麻植物的纤维或蚕吐的丝),并通过加工将其转化为成品。政治经济学家对同时鼓励农业和工业部门的潜力表示赞赏(在这方面,中国的发展理念与其有相似之处)。但在欧洲许多地区,这些干预措施只能预见两大部门的市场导向,而不是生存。
例如,在18世纪中叶,托马斯·普雷尔(Thomas Prior)发表了一篇为爱尔兰经济发展提供建议的文章,题目为《鼓励和扩大爱尔兰亚麻制品加工》,就明确地阐述了这一点。在这篇文章中,普雷尔详细核算了利润和经济增长如何从国内鼓励的亚麻行业流向出口市场。由于“那些行业大多使用手工,由国内材料加工,并在国外寻求市场,最应该得到鼓励……因此我们的注意力应该放在增加纺织机的数量和提高亚麻的质量上”[21]。对纺织业的鼓励使政府当局能够直接深入家庭,将其作为原料和成品的生产基地,并在当地建立新的性别分工。普雷尔还阐述了他想象中的纺纱工人:“根据经验,我们发现,一个年轻的妇女,或一个九岁的孩子,可能在六周或至多两个月的时间里学会纺纱三四打。”[22]
远在南方的西班牙,1774年另一位政治经济学家也提出了类似的观点。佩德罗·罗德古兹·德·坎波曼斯(Pedro Rodríguez de Campomanes)发表了一篇备受欢迎的关于工业的论文,最终由西班牙国王进行传播。卡门·萨拉苏阿(Carmen Sarasua)认为,这篇论文“提倡把农村工业作为国家经济复苏的最佳战略”。农村工业使人们能够将农业和工业结合起来,解决季节性农业失业问题,防止移民涌入城市(从而导致政治动荡),并保持工业工资的低水平”[23]。
尽管这些动力在多个纺织行业都发挥过作用,但我们将特别关注丝织业。法国丝织业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法国政府对丝绸生产的支持显然很早。在15世纪,丝绸传入法国南部,到了17世纪初,法国政府对经济发展产生新的兴趣,鼓励力度加大,因而桑树种植面积扩大。国家提供园艺和技术咨询,并建立丝绸检验机构,保证各生产阶段的质量。1665年,克里斯托弗·伊斯纳尔(Christophe Isnard)出版了一本指导植桑、养蚕和纺生丝的书。伊斯纳尔把这本书献给了法国财政部长让-巴蒂斯特·科尔伯特(Jean-Baptiste Colbert)。伊斯纳尔出版这本手册,是为了支持法国政府对丝织业项目的鼓励。[24]到18世纪末,以东南各省的小缫丝作坊为基础的丝绸生产,每年产值达到1.3亿里弗(古时的法国货币单位及其银币),约占法国工业总产量的15%。
由于丝绸在18世纪是法国的主要工业,丝绸织物的质量不仅关系到企业家和纺织工人,也关系到国家。在18世纪中叶,被路易十五任命为丝绸生产督察的雅克·德·沃坎森(Jacques de Vaucanson)为一种新纱锭申请了专利,并在法国科学院和国家的支持下将其推广。萨拉苏阿提出,沃坎森的发明对法国乃至整个欧洲的丝织业都产生了立竿见影的效果,并被狄德罗(Diderot)著名的《百科全书》称赞为最好的缫丝设备,因为它“保证能纺出更清洁、更细的线和更高质量的丝,有助于生产更具竞争力的丝绸”。[25]沃坎森也参与了织机的创新。
除了对该行业技术的关注外,劳动力的技能对生丝企业的盈利能力以及最终丝织品的质量至关重要,这些技能包括真空吸尘器和纺纱机,即妇女从蚕茧中解开和扎牢珍贵丝线的能力。[26]生产的快速增长意味着技术熟练的纺纱工人经常供不应求。在原材料如此昂贵的丝织业中,一个技术不熟练的织工就是一场灾难。1773年,一位法国“公民”在呼吁政府监管丝绸工厂的提案中强调法国丝绸制造商的担忧,就像竞争对手意大利之前所做的那样,他写道:“这个(工厂)主肯定会出售他的生丝……赶紧让它纺纱……他的工厂由一台状况不佳的单轮纱锭设备组成,由缺乏经验的纺纱工来操作。纺纱工不是按质量对茧进行分类,而是不加选择,几乎也不清洗,就把它们扔到洗涤槽里。由于缺乏规律和持续地纺纱,不同股数就拧成了丝线,这就产生了有缺陷的丝绸,为此,工厂主、制造商和织工必须承担损失。”[27]与他的呼吁同时,法国几个城市的丝绸制造商签署了请愿书。大家一致认为,在生丝生产缺乏足够规范的情况下,政府通过补贴、赏金等方式鼓励丝织业的做法纯属浪费时间。需要注意的是,除了潜在地设想企业家有权期望国家干预以支持其市场竞争优势外,他们的语言中还隐含了关于劳动力性别化本质的设想,即他们希望提高技能。
无论新技术还是旧技术,采用它们的工人在性别上从来都不是中立的。在国家直接或间接的鼓励下,关于年龄和性别分工的设想在整个欧洲被引入或被制度化,如我们在前文中提到的爱尔兰亚麻工业中对女性和儿童劳动的强调。就法国丝织业而言,专家的技术咨询流通也带来了关于年龄和性别分工的设想。伊斯纳尔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第二人称的直接称呼,这似乎是在假想他的听众大多是男性,其中包括野心勃勃的农户领袖、地方行政官员和学术团体成员,他们有可能真会把他提出的推动当地丝织业发展的建议付诸实践。他用男性的职业头衔来描述丝绸生产的各个过程。但是,他含糊其辞地提到了“拉丝工”和“纺纱工”(都用男性形式),他们需要男人或男性侍者的协助把生丝缠到线轴上。他所描述的这个过程清晰地显示出“纺纱工”是女性。[28]

图1 丝织工业:缫丝和“皮埃蒙特之旅”,丹尼斯·狄德罗和让·勒朗·达朗贝尔编:《百科全书,或科学、艺术和手工艺分类辞典》
后来的手册和百科全书的描述——其中最著名的是18世纪由丹尼斯·狄德罗(Denis Diderot)编辑的《百科全书》——通常使用女性代词和女性词尾,这揭示了他们认为缫丝和纺纱工人是女性的设想。这一文本并非是国家政治的产物,但是其关于技术的文章和随附的插图,反映了法国和欧洲的农业和工业领域最先进的知识,并在经济发展领域广泛流传。关于丝绸的主要文章《丝织品》(Soierie)中有一幅缫丝图片,显示了与房子相邻的农村院子里缫丝的场景(图1)。在1772年的原始版本中,图片下方的文字对工人的描述非常明确:“这幅插图展示了从蚕茧中抽出丝的过程,以及两个忙碌的女孩(filles)——一个在卷轴的曲柄处,另一个在大锅旁。”前者后来被称为“缫丝女工”,后者则简单地称其为“工人”,但两者都使用了女性词尾。
这些设想一直持续到19世纪早期。例如,经济学家、法国副总统、经济发展专家弗朗索瓦-费利克斯·法雷尔(Francois-Felix de la Farelle)就曾这样描述19世纪早期法国南部的原始工业生丝生产。他写道:“第一个女工,被称为‘纺纱工’,她能非常灵巧地把(丝)架(从蚕茧上)剥离下来,至今仍然如此。第二个女工转动纺轮,并被冠以‘缫丝女工’的称号。从事生丝纺纱的妇女和女孩既在小的家庭式作坊中工作,也在‘宽敞的厂房’中工作,厂房工人多达50人,俨然‘一个初具形态的制造厂或手工业工厂’。”[29]
同样值得注意的是,国家干预的目的可能是改变和重新书写现有的性别分工。卡门·萨拉苏阿(Carmen Sarasua)在她关于西班牙国王引进沃坎森的新纱锭的研究中发现,国家行为涉及一个蓄意改变现有性别分工的目标:
坎波曼斯模式最有趣的一点是他坚信恰当的性别分工对经济发展至关重要。相反,西班牙现有的性别分工是错误的,这是造成该国经济和社会落后的主要原因之一……不管怎样,在巴伦西亚(Valencia)地区,大多是男人在缠绕和缫丝,这就成为争论的关键,因为新的纱锭必须由妇女来操作……这意味着它的引入将使现有的劳动分工发生彻底改变。奥尔特(Ortells)认为,这既是新纱锭的主要优势,也是妨碍其采用的主要障碍。[30]
在整个18世纪,在法国和西班牙的丝绸生产,以及爱尔兰的亚麻生产过程中,国家干预不仅支持了技术和企业的创新,而且还传播和强化了关于特定年龄和性别的雇工策略的观念,以满足这些行业的需求。
欧洲国家统治者通过多种战略与纺织工业建立了更直接的联系。这其中包括国营的“制造厂”,即雇用手工业工人生产符合国家利益的商品的企业。但是,其他形式的干预产生了更广泛的影响——也就是说,通过国家许可的垄断形式,个别企业家或企业家的公司与国家合作发展原始工业。由于从国外购买丝绸似乎明显是在消耗国家的财政收入,德意志多位国王都试图在国内建立丝织业。
这种形式的国家经济干预,有一个很好的例子,那就是位于莱茵兰的德意志普法尔茨(Kurpfalz)选侯国。这种做法始于17世纪末,持续到18世纪末。1664年,一位名叫贝彻(Becher)的丝绸推广商从选帝侯那里获得了丝绸专卖权,还得到了能种植两万棵桑树的土地。1700年左右,这一丝绸推广计划因战争而搁浅,但这个想法并未遭遗弃。1728年,选帝侯卡尔·菲利普(Karl Philipp)把意大利生丝栽培者带到了普法尔茨,试图建立丝织业;他还租给他们丝绸特许权,包括要求当地贵族地主植桑养蚕的权利。得到国家批准后,地主试图强迫农民植桑养蚕。农民在传统的劳动之外,又要被迫接受新的劳动要求,他们非常愤怒地提出抗议,并设法让大公禁止新丝织业的强制无偿劳动。由于强制没有奏效,这个项目几乎没有成功。
1748年,新选帝侯卡尔·西奥多(Karl Theodor)再次尝试,并提供了20年的垄断权。与之配套的是,还成立了一个国家丝绸机构,提供园艺咨询。但是,由于对一种非食用作物的长期投资本质上是一种高风险的投资,没有利润保证,农民几乎没有什么兴趣。因此,1758年,国家再次采用高压手段,设立了“丝绸委员会”。这个等级森严的国家官僚机构在每个村庄都设立了官员、地区检查员和监督员。每个居民都必须种植一定数量的桑树;此外,还根据每个村庄的人口对其实行集体配额。这种强制策略又一次遭到了农民更为强烈的反对,强制执行配额的尝试引发了无数的抱怨和请求豁免的请愿。许多农民因毁坏树木、放牛吃树苗或最初拒绝种植桑树而被捕或被罚款。凑巧的是,这个最后的计划在法国大革命初期也失败了,当时砍伐桑树将其当作木柴来烧在当地成了一种特定的反叛形式。这个国家一再强迫农民家庭从事奢侈的纺织业生产,但收效甚微;而且,他们不是邀请农民加入,而是使农民家庭与国家的“经济发展”计划更为疏远。[31]
18世纪下半叶,选帝侯卡尔·西奥多也曾试图发展丝织业,但成败参半。他为法国和意大利丝绸产区的几位企业家提供补贴、场地和其他形式的支持,帮助他们在普法尔茨的几个城市建立“工厂”。最初的想法是生产丝织物和长袜,以满足宫廷的需要,从而减少对昂贵的奢侈丝织物的进口。但似乎唯一经济上可行的创新,是1780年代为满足当地消费甚至出口而生产纱线的纺纱厂。值得注意的是,这次引入的模式不是原始工业典型的家庭生产模式,而是以城市为基础、大“工厂”的新模式。工人们为了就业不得不移居城市,这就是后来的工厂模式。即使这些试验性工厂的纺织部门——大部分是基于男性劳动力而设置——停滞不前,但由国家资助的最成功的企业家让·皮埃尔·里加尔(Jean Pierre Rigal)开创的纺纱厂却迅速发展起来。工人数量从1774年的76人(其中织袜工大约占一半)增加到1775年的93人(其中只有13名织工);当时75%的工人是女性,女性垄断了纺纱行业。到1786年,工人集中在纺纱行业,人数已超过400人。[32]这项由国家赞助的实验预测了欧洲纺织业的未来,无论是在设置有薪的女性工人,还是将这些工人从农村家庭转移到城市的工厂环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