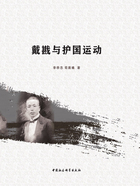
前言
戴戡(1880—1917),贵州贵定人,原名登荣,字锡九,后改名为戡,字循若。[1]戴戡短暂的一生,经历了民初以来贵州、西南、全国以及东亚舞台上的一系列动荡和变化。他出生、成长于偏僻落后的贵州农村地区,直至二十四五岁时获得机会东渡日本留学,才逐渐跻身于新式知识分子之列。回国后最初几年,他仍然显得默默无闻。民国成立以后,他迅速走向政治前台,担任过贵州最高行政长官。随后袁世凯加紧复辟帝制,戴戡则追随梁启超、蔡锷,参与策划并在云贵两省发动护国战争,与蔡锷并列为西南战场上的两位主将,由此在民国政治史和个人生命历程中写下了亮丽的一笔。护国战争结束后,戴戡被任命为四川省长,不久又兼代四川督军,成为西南乃至全国政坛的重要人物。然而成为四川最高军、政首脑不到三个月,戴戡就在与川系的冲突中兵败身亡。身故之后,北京政府表彰他“见义勇为,持正不阿”“拥护共和,厥功尤伟”[2],追赠为陆军上将,生平事迹交付国史馆立传。
护国运动是民初历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被孙中山视为继辛亥革命和二次革命之后的第三次革命。对于这场爱国运动,学术界已有不少研究。孙中山和中华革命党人、黄兴和欧事研究会成员、梁启超及蔡锷和进步党人、唐继尧和西南军阀等力量在其中扮演的角色、发挥的作用,均得到了较为详细的呈现。[3]关于戴戡在护国运动中的事迹,以往的各种论著也多有提及[4],不过相关叙述或者失于简略,或者显得零碎,不少论断还不无偏见。近年来,有的学者注意到这个问题,尝试着摆脱当时敌对阵营人士的党派偏见以及后来极“左”思想的影响,对戴戡进行更加客观公允的评价,认为戴戡在历史关键时刻立场正确而坚定,大节铮铮,在反对帝制、再造共和的护国战争中表现英勇、卓有功绩;以往那种将贵州辛亥革命之失败归咎于戴戡“引滇祸黔”的观点缺乏说服力,把戴戡的一言一行都视为阴谋,甚至编造事实将他肆意丑化,这种做法并不符合实事求是的精神。[5]
总的来看,戴戡大体属于今人眼中那种“非主流”的清末民初历史人物。他的生平经历,目前仍然不太为人了解和理解。他如何从地处边陲的贵州崛起并成为一位全国性的精英人物?民初主政贵州期间有何建树?特别是他在护国运动前后的经历,至今未能得到充分呈现。他何以能够成为护国运动的主将之一?在这场运动中具体发挥了什么样的作用?护国战争结束后,他作为贵州人率领部分黔军入主四川,最后在与川系的竞争和冲突中不幸丧生。以往一般认为这是军阀割据混战局面的开端[6],那么事情是否如此简单?其中是否还有着更加复杂的深层次内容?这些问题的解答,都有待于对其生平和时代进行深入细致的探讨。
研究戴戡这类今人眼中的“非主流”清末民初历史人物,有两方面的困难需要认真对待。一方面是史料。20世纪的最初二十余年,是中国历史上一个翻天覆地的大变革时代。这一时期涌现了许多杰出的历史人物,他们一度走在时代的潮头,乃至扮演了时代的主角。可是不出二十年,其中不少人便退出了时代舞台,只留下依稀的历史背影,在后来的主流历史叙事中被边缘化。戴戡即属于这种情况。他出身于贫寒之家,关于他的早年生活和成长经过,目前所能获得的一手史料极为匮乏,可供参考的主要是家族后人及亲友故旧留下的口述资料,由于时隔多年加上辗转相传,其中一些信息难免有失确切。辛亥革命以后,戴戡迅速崛起,在西南地区和全国政坛产生了重大影响,相关经历和行事在官书档案、函电书札中多有踪迹可寻,不过总体上仍然显得零碎。更加具体的情况,可供参考的主要是当时的报纸杂志,以及当事人后来的回忆性撰述。不过,报纸杂志的报道并非绝对准确,不乏道听途说、捕风捉影的成分。回忆性的撰述往往产生于几十年之后,经过文字加工刊载于各级文史资料,并且有的系由对立派别人士所撰,回忆失真和意见偏颇的因素在所难免。总体而言,相关史料呈现了大致相反的两个特点:准确度较高的一手史料,能够提供的信息往往较为简单、零碎;能够提供较为详细信息的,又往往是辗转相传的二手、三手史料。因此,在研究戴戡这样的历史人物时,既需要花大力气尽可能去搜集直接的一手史料,更需要对相关史料特别是二手、三手史料提供的信息多方比对,细心揣摩,审慎运用。
另一方面是史识。清末民初这段历史颇为复杂,传统与近代、改良与革命、中央与地方、统一与分裂、文士与武人,种种矛盾群集。长期以来,人们习惯于简单僵化的二元对立思维,以革命派为中心展开历史叙述,对相关事件、人物的评价非黑即白,不是进步就是反动,不是革命就是反革命。在这种历史认知框架下,不断探索渐进式变革路径的梁启超,长期以来曾经被视为略带负面色彩的人物,未能得到应有的重视;跟他关系密切的同时代许多精英人物,包括戴戡在内,也遭到有意无意地贬抑甚至丑化。其实,僵化的思维并不能缚住已经故去的历史人物,而只会困住生活在当下的今人自己。站在21世纪的今天,着眼于中国社会的现代化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回顾过去一百多年的历史进程,无疑有必要进一步摆脱简单的二元对立思维,摆脱政治路线分歧的因素,立足史料,尊重史实,尽可能做出客观公允的论述。这既是对历史人物应有的态度,同时也是对今人自己负责。
[1]戴汝愚等:《戴戡行述》,卞孝萱、唐文权编著《辛亥人物碑传集》卷五,凤凰出版社2011年版,第211页。后来一些论著称戴戡原名桂龄,号锡九,均误。《戴戡行述》撰于戴戡身故后举办葬礼期间,以戴戡之子戴汝愚、戴汝次的名义刊印,实际撰稿者为戴戡的亲友故交,他们当时的记载应该比后人辗转听来的说法更加可靠。
[2]《八月十七日大总统令》,《申报》1917年8月19日第2版。
[3]参见谢本书等编著《护国运动史》,贵州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谢本书、冯祖贻主编:《西南军阀史》第一卷,贵州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4]相关成果主要有戴聚懿《再述戴戡事略》,《贵定文史资料选辑》第2辑,1983年;谢本书等编著《护国运动史》,贵州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12—113、128、141、143、175—176、216—218、375—376、380—382页;丁宜中《我所知道的戴戡》,《贵州文史资料选辑》第25辑,1987年;黄发政《护国战争时期的戴戡》,《贵州师大学报》1987年第3期;胡端楷《戴戡》,《贵定文史资料选辑》第6辑,1992年;龙之鸿《戴戡的一生》,《贵州文史丛刊》1993年第3期;刘毅翔《戴戡、任可澄与护国运动》,《贵州社会科学》1996年第1期;邹芝桦《护国将军戴戡》,贵州省政协办公厅编《文史天地》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特刊,2011年;马宣伟《戴戡》,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编《中华民国史·人物传》第二卷,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532—546页。
[5]李中:《戴戡试评》,《贵州文史丛刊》2011年第3期。
[6]谢本书、冯祖贻主编:《西南军阀史》第一卷,贵州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4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