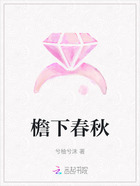
第4章 檐角风吟
黔州的秋末总蒙着层雨帘,青石板路像浸在墨水里的宣纸,连空气都泛着冷冽的草木香。我蹲在幼儿园花坛边捡枫叶,陈老师举着手机凑过来,屏幕上的文旅推文里,沈砚之穿着深灰风衣立在古巷口,胸前的银杏胸针闪着细银线,像他每次见我时欲言又止的眼神。
“你们真没联系?“陈老师戳了戳我发怔的脸。枫叶在指尖碎成红点,我想起三天前在园门口,他抱着木箱匆匆而过,风衣下摆沾着泥点,银镯在腕间晃出半道弧光。那时我正给孩子们分发绘本,他隔着栅栏喊了声“苏郁“,却被孩子们的喧闹声盖过,最终只冲我点了下头,转身时银杏胸针擦过木箱边缘,划出细微的声响。
周四下午,我抱着教具箱路过园长办公室,听见沈砚之的声音从门缝里漏出来:“圆角处理要做到两毫米,防止孩子磕碰。“脚步顿在走廊,箱底的橡皮泥飞檐模型滑出一角——上周突然出现在储物间的木质斗拱教具,底座那枚“榫卯“小楷,此刻忽然有了温度。
“苏郁?“他推开门时,藏青卫衣上沾着片银杏叶,胸针别在第二颗纽扣旁,露出别针处极小的“砚“字刻痕。“来交资料?“他伸手扶住我倾斜的箱子,指尖触到橡皮泥时忽然笑了,“上次见孩子们用这个捏斗拱,说比课本上的好玩。“
他从风衣口袋摸出个铁皮盒,推到我面前:“给孩子们的。“里面是十二枚银杏书签,叶脉间嵌着细银线,在走廊的阴翳里泛着微光。“我奶奶寄来的嵌银工艺。“他补了一句,低头看了眼手表,“团队后天去测绘吊脚楼,可能没空再来。“
攥着书签的手忽然收紧。我想起他曾说奶奶是退休教师,总在江南的老院子里教孩子们刻木雕。储物间的糖杨梅罐、暴雨夜的AR绘本,原来都藏着他没说出口的牵连。路过操场时,他单膝跪地检查秋千支架,深灰风衣扫过草地,我别过脸不去看他腕间晃动的银镯,指甲掐进掌心。
暴雨来得毫无征兆,傍晚整理玩具柜时,才发现沈砚之的三个未接来电。我攥着手机往铁栅栏外跑,雨水砸在脸上,却在看见他深灰身影时猛地停步——他怀里的牛皮纸袋裹着防水布,银杏胸针在雨幕里忽明忽暗,像极了我每次看见他时慌乱的心跳。
“AR绘本,扫描封面能看3D古戏楼。“他的声音被雨声打散,我隔着栅栏接过纸袋,指尖触到他掌心的温度。“姜茶在保温杯里,“他补了一句,耳尖红得比枫叶还鲜艳,“奶奶说雨天要喝热的。“
储物间里,他摆放纸袋的动作轻得像在修复古建,忽然打了个喷嚏。卫衣帽子滑下,露出额角旧疤,我想起他曾说那是小时候在爷爷的戏曲小院爬雕花梁留下的。“其实我......“他开口时,我慌忙掏出水果糖塞给他,指尖擦过他掌心的茧,像触到测绘图上的墨线。
“小雨说书签很喜欢。“我盯着他胸前的银杏胸针,故意忽略他欲言又止的眼神,“以后不用特意送东西来,幼儿园采购很方便。“他捏着糖纸的手顿住,喉结滚动着没说话,窗外的雷声盖住了储物间里突然的沉默。
周末的酸汤鱼馆飘着木姜子香,我在衣柜前摸过藏青连衣裙,最终选了素白衬衫——上次他的目光停留在藏青布料上,此刻却成了我刻意避开的证据。戴上阿婆的苗银镯时,镜中的自己眼神躲闪,像在逃避某种注定的告别。
沈砚之坐在窗边,面前摆着紫砂壶,见我进来时起身替我拉开椅子,袖口的刻刀伤痕又深了些。“黔州水质硬,“他倒茶的手悬在半空,“奶奶说米茶养胃。“我盯着他腕间的银镯,想起他曾说那是奶奶用陪嫁银料打的,忽然开口:“以后别寄东西了,孩子们会依赖。“
他倒茶的手一抖,茶水溅在杯沿。陈默的笑声从身后传来,拍着沈砚之的肩膀嚷着“给苏郁讲讲你奶奶的木雕“,他却低头搅着酸汤,说:“奶奶退休前是教师,总说木头和孩子一样,要慢慢打磨。“我捏着筷子的手收紧,酸汤的辣味刺得眼眶发烫,原来他早已看透我刻意的疏远。
陈默醉倒后,包间里只剩我们两人。沈砚之摸出小木盒推过来,木质牡丹胸针躺在丝绒里,银线在灯光下泛着柔光。“奶奶说金缮牡丹......“他声音很轻,我却打断他:“我知道,碎过的地方才结实。“别胸针时,他的指尖擦过我锁骨,迅速收回,像触碰易碎的古建构件。
离别的那天,黔州下着蒙蒙细雨。我站在幼儿园门口,远远看见沈砚之的车停在巷口,后窗的卡通贴纸被雨水冲淡。陈老师叹气:“不去送送?“我摇头,攥紧口袋里他送的银杏钥匙扣,金属边缘硌得掌心发疼。
手机震动,他发来消息:“巷口银杏树下有给孩子们的礼物。“树洞里的小木盒里,是十二枚刻着古建纹样的橡皮章,便签上的字迹被雨水晕开:“苏郁老师收“。我摸着橡皮章上的斗拱,想起他曾说古建修复是“让破碎的时光重新呼吸“,此刻却觉得这呼吸里藏着太多未说的话。
车的尾灯消失在雨幕里,我转身走进幼儿园,孩子们举着枫叶问:“胸针哥哥呢?“我笑着给他们分发橡皮章,说:“他去修更远的古建了。“不知哪个孩子把银杏叶放在我掌心,叶脉间的细缝像极了沈砚之测绘图上的留白。
此后每月十五,总会收到匿名包裹:木质教具、蓝印花布书签、奶奶腌的糖桂花。我对着包裹单上工整的字迹发呆,最终在回执里写:“谢谢,孩子们很喜欢“。渐渐的,包裹里多了些江南的小物件:绣着戏曲纹样的帕子、刻着童谣的木雕笔......却再没出现过他的只言片语。
深秋路过老城巷口,那棵银杏树的树洞被改造成“古建知识角“,玻璃罩里摆着微型斗拱,旁边是沈砚之的手绘图:“榫卯咬合时,风会记住它的形状“。树下的小女孩指着模型喊我:“苏老师,这是不是胸针哥哥做的?“
风穿过檐角,吹落最后几片银杏叶。我摸着腕间的苗银镯,忽然想起沈砚之朋友圈的最新动态:一张江南戏曲小院的照片,配文“爷爷的戏台上,奶奶种的桂花开了“。照片里,穿蓝布衫的老太太正给孩子们分发木雕书签,背景是雕花梁上的银杏纹样。
原来有些温柔不必说破,就像他嵌在测绘图里的惦念,我藏在回执单里的谢意,都在时光的榫卯间,悄悄咬合。或许某天,江南的桂花香会随着秋风漫过黔州的巷口,而我会指着银杏树上的阳光,告诉孩子们:“看,那是时光给温柔的回信。“